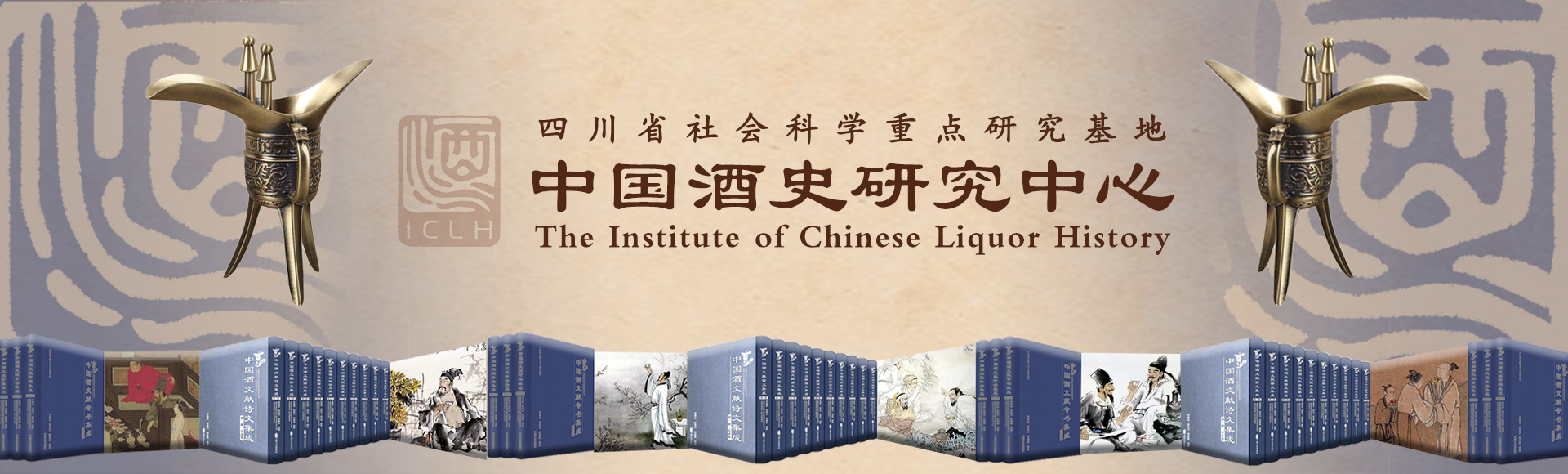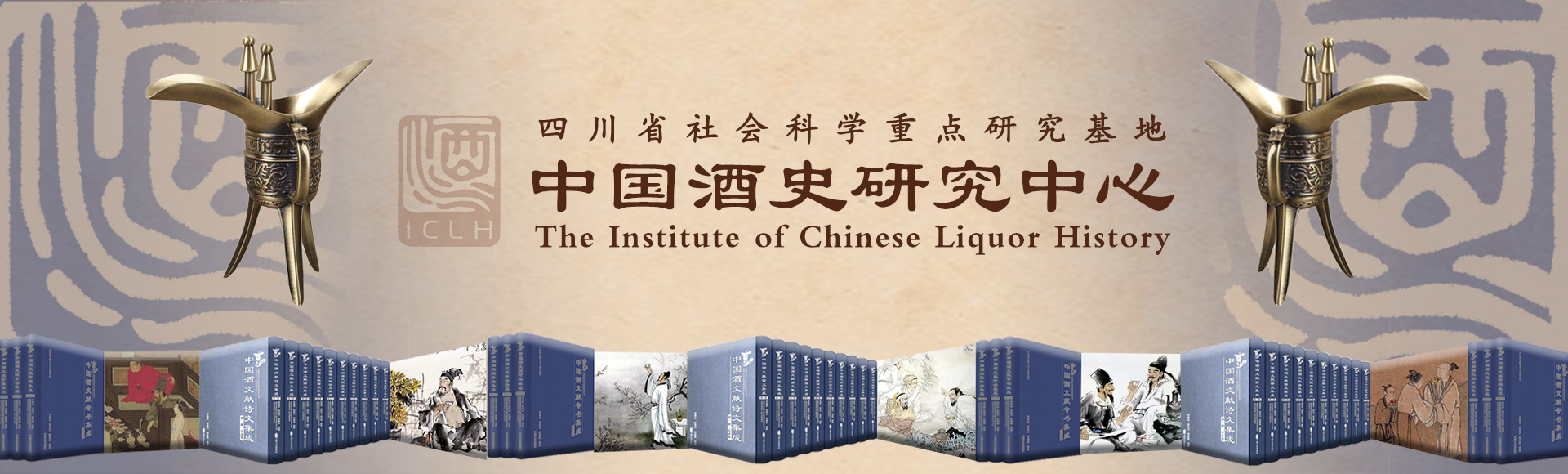我是戒了白酒的,戒得一口白酒也不喝。
我喝啤酒,而且是天天晚餐喝一瓶。一家三口,妻子和孩子不沾这东西,我一人独酌。
戒白酒是工作需要。曾在一个常要陪人吃饭的岗位上呆过,一口酒不吃,开始得罪了人,后来真的是每回都一口不喝,于是每次都会有人出面帮助解围。我也不是从没有喝过,只因前些年不愉快的事太多,弄出个胃溃疡,不能不戒了白酒。说是怕死,也还不是,人总是要死的,只是万一真的哪天一不小心,喝得胃出血,死在餐桌上,实在是不得其所。
我这个人虽被人称作诗人,但一遇到以酒论诗的场合,就自愧不如了。别人的诗是不是洒醉后写出来的,不好妄下断言,我这半辈子写的诗也上了千首,有办公室里写的,有听报告时写的,有坐火车乘飞机写的,还有睡到半夜梦中得一佳句翻身写下接着再睡的,各种情形下均可写作,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有这个随遇而安的写作心态,唯独没有酒醉后写的诗。
虽然我没有酒醉后写的诗,但我酒醉过,这说明我是与酒有过深交的,因此我也写过关于酒的诗,写得不好,这倒恐怕是因为没有在醉态中写酒,不得其魂魄。
人们说到酒,常常与宴会之类的事联系起来。叫我说酒,那些闹闹哄哄的饭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记忆,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一次。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在延安军马场当仓库保管员。一次哄抢拖拉机的事件中,我无意中当了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那次事件后,朋友们为了感谢我,在马场办的酒厂当保管员的一个知青提来半桶刚出锅的玉米烧酒,把我灌得舌头发直,喝酒如同喝凉水,最后是晃晃悠悠出了门,一迈腿,躺进了水沟里。
在这个事件之前,我对酒毫无畏惧。在我刚十八岁那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我因是“黑帮子女”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于是我找了三个跟我境遇差不多的同学“长征串联”。四个人,三个多月,六千七百里步行到北京!其实,那时我们走得很苦但并不认为有什么办不到。我们是十月下旬从家出发,在陕北延安过的元旦,到北京已快过春节了。几个月在寒冬里跋涉,为了驱寒,为了解乏,我们背着的军用水壶里总是装满老烧酒。冷了,咕咚两口,累了,咕咚两口。那时,与酒的感情真是一言难尽,患难之交啊……
唉,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在满桌大鱼大肉中的酒,已没有当年那份韵味了,苦,且上头。也是的,好日子来得也不易,叶氏酒话已是老话,老话不说也罢,还是啤酒随和,体味着清凉中的那丝苦味,安慰自己:也曾年轻过。年轻时的烈酒点燃的不是欲望而是勇气,这就足以向着青春往事,轻松一挥手,去吧!自信人生不是一桌筵席,中年也不是一只空酒瓶……
(选自《闻香识酒》,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