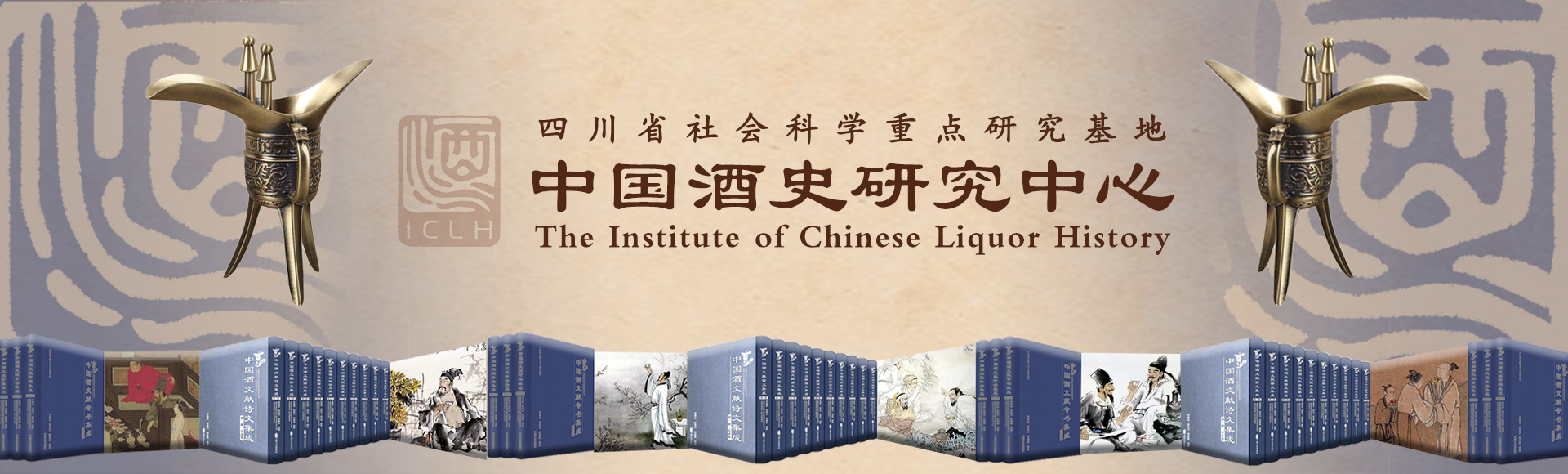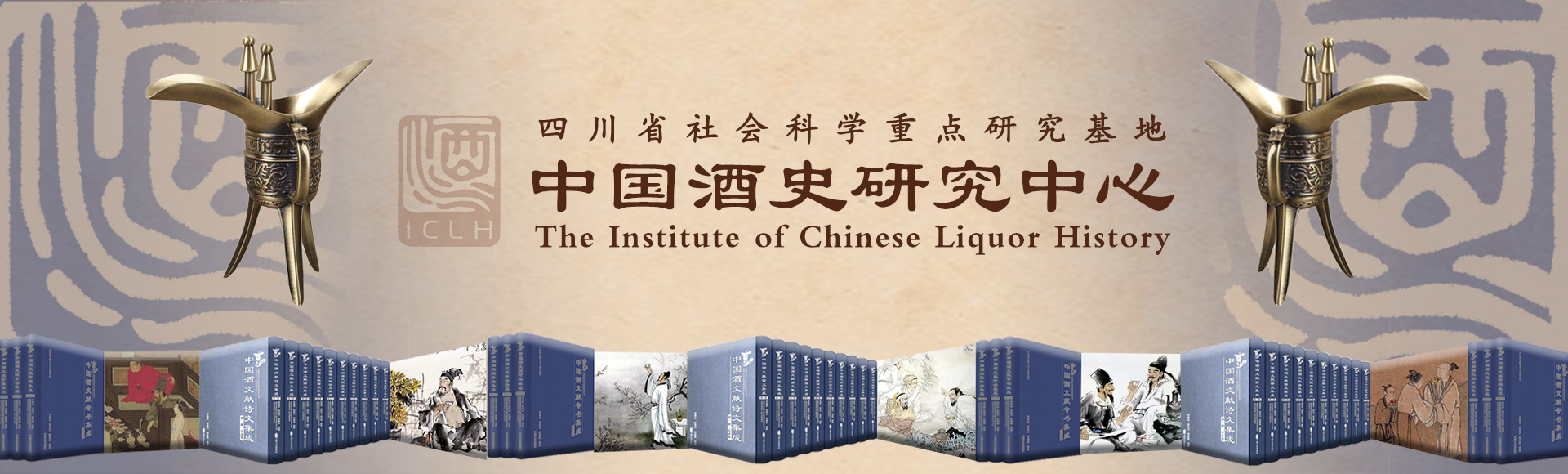酒令起源甚早,大体说来,春秋战国时已经产生。台湾学者陈香有谓:“酒令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创的,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气息相关。酒令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同好的,和我们的生活习俗紧密交融。”所言甚是。酒令的形式纷繁复杂,内容也是异彩纷呈,形成的专书即有《令圃芝兰》、《庭萱谱》、《小酒令》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详述。综观明朝酒令,与前代酒令一样,不仅富有文学色彩,而且充满人文气息;从明朝酒令中,我们往往能窥知当日世风民情,虽然饮酒行令,主要目的不过是助酒兴,增加欢乐气氛。何良俊曾谓:
饮酒亦古人所重。诗日:“既立之监,复佐之史。”汉刘章请以军法行酒,唐饮酒则有觥录事。今世既设令官,又请一人监令,正诗人复佐之史之意也。
如此看来,明朝行酒令时,是一本正经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行酒令常常离不开酒筹。此物也很古老。唐朝人的诗中即曾描绘“城头稚子传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分明写的是吃酒时催花猜拳。古入饮酒时,用牙制成箭,长五寸,箭头刻鹤形,称做“六鹤齐飞”,用以行令;明代行酒令的牙筹,大致与古人同。
击鼓催花令,在明朝的文人圈里,是很盛行的。李东阳(1447-1516)在一次宴席上,曾用此令戏成七律一首:
击鼓当筵四座惊,花枝落绎往来轻。鼓翻急雨山头脚,花闹狂蜂叶底声。上苑枯荣元有数,东风去住本无情。未夸刻烛多才思,一遍须教八韵成。
第三、四两句,描写击鼓催花的情景,极为传神。
万历时的田艺蘅也爱好酒令。某次,他与几位骚人墨客在中秋节边饮酒、边赏月,并有一位叫玉蟾的妓女陪席。忽然有轻云遮住了月亮,田艺蘅便作四声令“云掩皓月”,以羽觞飞巡,并不断轻击酒罐,以四声为韵催之,如不按韵,罚酒一杯,如不成句,罚酒四杯。结果,随着羽觞的飞传,在阵阵酒罐声中,在座的客人有的说“天朗气烈”,有的说“秋爽兴发”,也有的说“蟾皎桂馥”、“风冷露洁”、“情美醉极”等,因为限于四声,不许有一字重复,此令的难度是很大的。所幸座客均为文士,并有捷才,所以能很快地念出上述种种四句酒令来。但最为难得的,还是玉蟾,她开口不离本行,念道:“行酒唱曲”,虽是日常口语,但按韵合调,无怪乎田艺蘅等盛赞她“不孤雅会,可谓俊姬”了。
酒令贵乎自然,前提是必须有很好的文化素养,弄不好,就会贻人笑柄。万历时,有个叫王文卿的人,其父是贡士,其叔是举人。可惜父早死,他便失学了。古诗有云:“月移花影上栏干”,文卿对这句诗半懂不懂,模模糊糊。有次偶尔参加一位姓邢的太史举办的宴会,行酒令时,要求说一物,包含在一句诗中。王文卿竟念道:“鱼花影上栏干”,引起举座大笑。席上有客人说:此令太难,无法相接,罚酒为宜。邢太史却胸有成竹地说:“我看不难。”便端起酒杯说:“鹦哥竹院逢僧话。”这里,他把古诗“因过竹院逢僧话”中的“因过”,改成“鹦哥”,不仅谐音,还与“酰鱼”对仗,真可谓巧夺天工。这也是无意抛砖玉却来的典型例子。当然,据载王文卿“侠气翩翩,亲朋皆称好人”,不会因在这次酒会中闹了大笑话,而就低人一等。好的酒令,幽默诙谐,读来令人捧腹。万历时著名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在苏州做官时,有位孝廉从江右来看他任部郎之职的弟弟,与宏道有同年之谊,宏道特地雇了一条游船,备了酒席,款待来宾,并请了县令江盈科(字进之,号绿萝山人)同饮。游船在绿水中缓缓行驶,宏道等频频举杯,酒兴正浓。客人请主人发一酒令助兴,宏道见船头摆着水桶,顿有所悟,便说:酒令要说一物,并暗合一位亲戚的称呼,以及与官衔符合。紧接着便手指水桶念道:“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员外的箍箍(谐音哥哥)。”他指的是孝廉是部郎之兄。这位孝廉见一船工手拿茗帚,便说:“此若帚非茗帚,乃是竹编修的扫扫(谐音嫂嫂)。”这时袁宏道的哥哥宗道(字伯修。1560一1600)、弟弟中道(字小修。1570—1624),都担任编修。江盈科正在沉思间,忽然看到岸上有人在捆稻草,便立即念道:“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总的束束(谐声叔叔)。”这是隐射某孝廉本来曾在军中效力,其族子某现在是武介。于是三人相顾大笑。相传明代还有互相拿姓名开玩笑的酒令。张更生、李千里二人同饮相谑,李千里先说酒令道:“古有刘更生,今有张更生,手中一本《金刚经》,不知是胎生?是卵生?是湿生?是化生?”张更生则反唇相讥,说令道:“古有赵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张、李二人,也堪称是开玩笑的能手了。
在明朝人的宴席上,有时以俗语作对,也不失为是有趣的酒令。有位布政使做宫忠于职守,不求引荐,当然也就得不到提拔。按照惯例,他进京朝见皇帝后,就要返回任所。他的同乡为一位侍郎设宴饯行,同一个部的人,都来会宴,这位应邀也赴宴的布政使就成了唯一的客人。饮酒间,席上有人见到此况,便开玩笑地出了一句上联“客少主人多”,要同饮者对下联。众人还未来得及开口,这位布政使却冲口而出:“某有一对,诸大人幸勿见罪。”念道:“天高皇帝远”,举座闻之愕然。显然,他对的下联,是舒愤懑。以他的政治身份,在京师这样的场合,竟说出这样的话,难怪使别人感到吃惊了。这类以俗语作对,涉及酒的,还有不少,诸如“酒肉兄弟,柴米夫妻”,“将酒劝人,赔钱养汉”,“茶弗来,酒弗来,那得山歌唱出来;爷在里,娘在里,搓来麻绳缚在里”等,流行于明代,均俱称绝对。
常言道:不平则鸣。在明代的某些酒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平者的心声。景泰时的陈询(1395-1460),字汝同,松江人,任国子监祭酒。陈询善饮酒,酒酣耳热,胸中有不平事,经常对人-吐为快。谁有过错,他当面指出,决不放过。在翰林院时,曾因得罪权贵,外放到安陆任知州。行前,同僚设宴饯别。席上有人建议行酒令,各用两个字分合,以韵相协,以诗书一句作结。座间陈循学士念道:“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谷学士接着说:“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念的却是:“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陈询为人耿直,不会吹牛拍马,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故在官场起而复路,很不得意。“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不仅是夫子自道,也堪称道尽了古今行直道而不走歪门邪道,却屡遭打击的耿介之士的愤懑。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民是对立的。民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几乎是无官不贪的本质。这在酒令中也有所反映。嘉靖时的学者郎瑛(1487—?),某次与群士会饮,席间有人倡议以盗窃之事作对联,算是行酒令,并带头先说:“发冢”可对“窝家”。接着有人说:“白昼抢夺”可对“昏夜私奔”。众人都说:“私奔,非盗也。”此人却辩解说:“这虽然名日上有些不伦不类,但仔细想想,私奔的原因不是偷了私情又是什么?”这自然是诡辩。又有一人说:“打地洞”可对“开天窗”。众人又说:“开天窗,决不是强盗干的勾当。”此人笑着解释说:“今天搜刮钱财的人,为首的又私自侵吞,这种开天窗的行径,与强盗又有什么两样?”众人哄堂大笑。又有一位说:“还有更好的对子呢,例如‘三槽船’正好对‘四人轿’。”众人听了不解,正在思索时,此人说:“三船固然载强盗,而四人大轿所抬的,不正是大盗吗?”众人更是大笑不止。这里的“开天窗”和“四轿所抬”云云,对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的大盗,作了辛辣的嘲讽。由此看来,不要以为酒令纯属消遣之物,其中也不乏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佳作。归根结底,酒令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欢乐,有愤怒,也有悲哀。
在明朝酒令中,冯梦龙和友辈夜欢,以《四书》句配药名为令,堪称奇绝:
“三宿而出画”:王不留行。“管仲不死”:独活。“曾哲死”:苦曾。“天之高也”:空清。“吾党之小子狂简”:当归。“裨谌草创之”:藁木。“出三日”:肉从容。“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天南星。“七八月之间旱”:半夏。“小人之德草”:随风子。“舟车所至”:木通。“以正不行,继之以怒”:苛子。“孩提之童”:乳香。“兴灭国,继绝世”:续断。“若绝江河”:泽泻。“亡之命矣夫”:没药。“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车前子。“有寒疾”:防风。“涅而不淄”:人中白。“胸中正”:决明子。“桃之天天”:红花。“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蝉蜕。“夫人幼而学之”:远志。
只有对《四书》烂熟,并精通中药者,才能作出这样典雅俏丽天衣无缝的酒令,今人只能叹为观止,望尘莫及了。
值得指出的是,明朝江南常熟吃酒行令,未免过于严肃认真,罚酒苛刻,使饮者如临深渊,简直成了灾难。嘉靖时吴县文人杨循吉曾记载:“常熟酒令至为严酷。”执令者如果发现谁杯中未饮尽,哪怕只有一滴,就要罚你饮一杯,如果有四滴酒,则要饮满四杯。饮者都对执令的酒录事唯命是从,不敢不喝。另外,饮酒的规矩又特别多,例如倘说话不检点、学饮不如法,都要罚饮,如被罚者辩解,就给你扣上扰乱酒令官的大帽子,罚满饮一大杯,倘再犯了规矩,则再罚,哪怕是已被罚了十次,饮了十杯,也决不宽恕。酒令官开始饮酒时,端起酒杯说:就照这个样子喝酒,才算合法。但当饮酒者照他的样子举杯饮酒,他又大喝一声,说你这种饮法不合法,罚你的酒。无怪乎杨循吉对此评论说:“其为深刻惨酷,殆杯勺中商君(按:即法家商鞅)矣。”酒席上居然冒出个刻薄寡恩的法家,是那样冷酷、不近情理,这实在让人费解。中国太大了!有些地方文化的怪异之处,真让人琢磨不透。所幸几百年过去,而今的常熟,别说这样的行酒令法,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恐怕常熟很少有人知道,其老祖宗曾经有过那样堪称咄咄怪事的行酒令之法,可见不合情理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1989年深秋,于秋风秋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