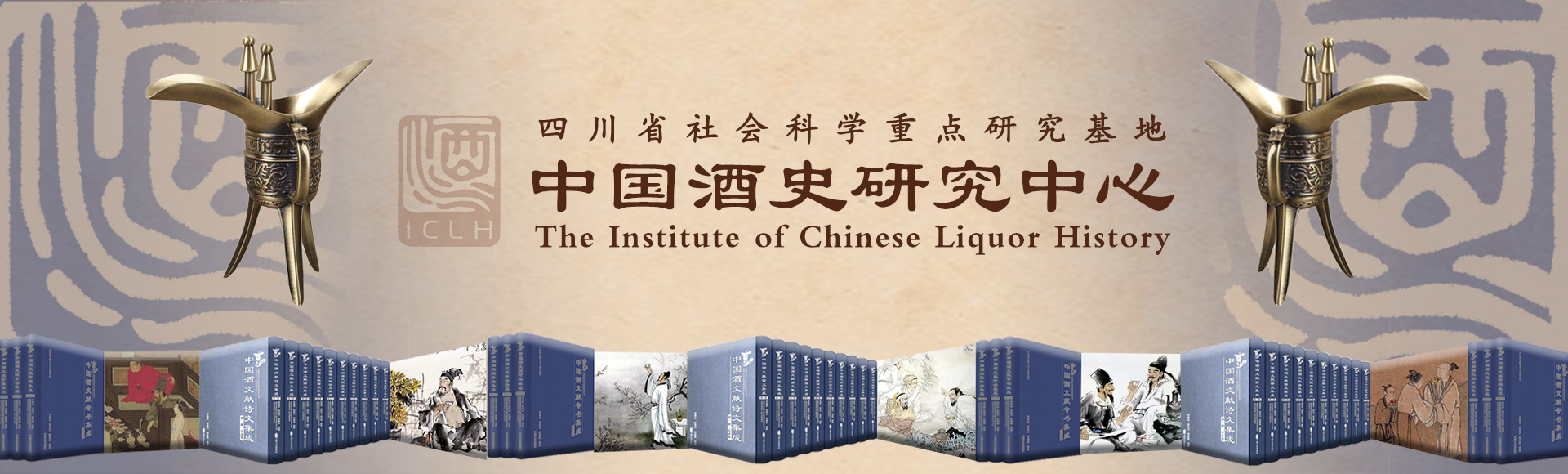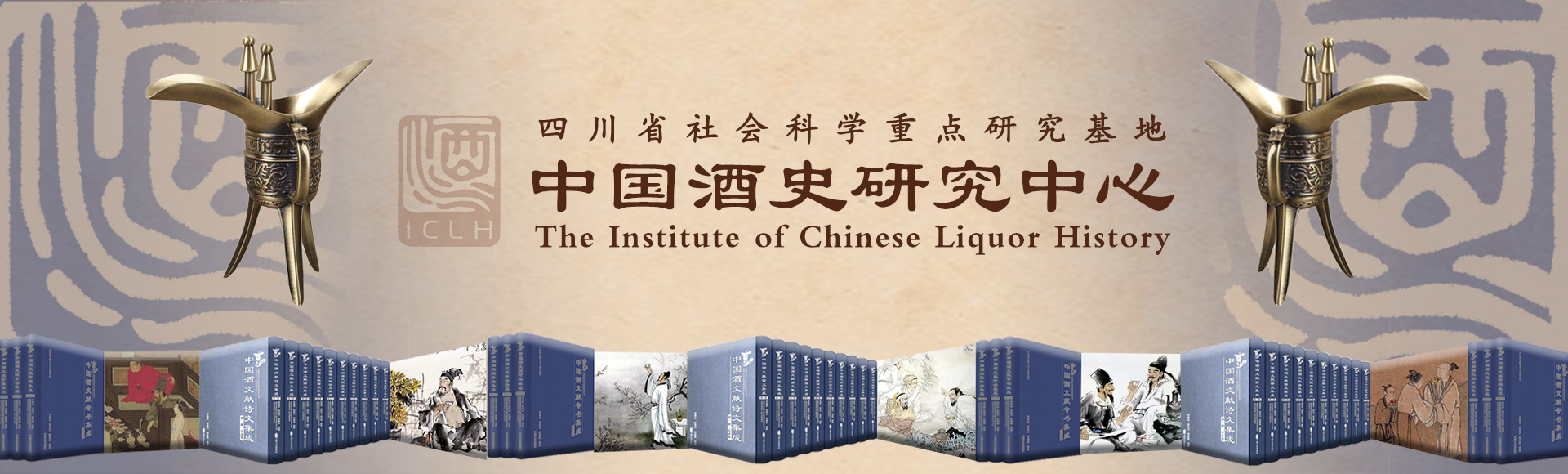我们常常在“吃饭”后面加上一个“难”字,在“喝酒”前面加上一个“学”字。吃饭难,学喝酒。
难的吃饭不去学,却去学喝那不说它难的酒,真是胡首。
奇怪的是,难吃的饭不学倒都会得吃,而且吃得十分地精。一旦没有了粮食,那就连树皮草根、观音土、健康粉、瓜菜大杂烩都能当做饭来吃,几乎能集天下之大成而吃之。至于那不难喝的酒,原是经不起大家去学的,就像软面团经不起大家压一样,会压出多种形状来,学出各种结果来。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以后,多少总能喝几杯了,但多到什么程度?少到什么程度?杯子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程度?差别很大,而且层次很多。就像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一样。还有两种人像两个极端,一种人总是学不会,功夫花得再深些也白搭,老是眼泪一滴酒便脸红耳赤,只得直认蠢材不讳。另一种人根本就没学,一试便发现自己是海量,乃是天生的英才。我还发现老天爷偏心眼,竟把这一类才能全批给了女人。男人则难得,或是被别的气质掩盖了也说不定。女人则表现突出,她跟那些好汉们坐在一桌,悄然敛容,除菜肴外,滴酒不尝。好汉们原也不曾把她放在眼里,总以为弱女子不胜酒,任她自便。后来喝得高兴了,热闹了,偶尔发现她冷冷落落,满杯的酒还没有动过,就举杯邀她也喝一点。她呢,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觉得不喝浪费掉可惜,只得略表谦逊,便含笑喝了那杯酒。却是一口、两口便喝光了。这可引起了大家的惊异。有人以为她没有喝过酒,错把它当开水喝了。而她竟脸不变色心不跳。于是一致看出她有量。正在兴头上的好汉们便不再可怜她纤弱,反如盯住了猎物不肯放过,一只又一只手捉着酒杯像打架般戳到她面前硬要干、干、干。她倒往往会打个招呼说:“我喝酒是没啥意思的。”可惜别人没有听懂,误会为“喝酒没啥意思”。认为说这种败兴的话还该多罚一杯。其实她说的没意思,是因为她喝酒像喝白开水一样,没有什么反应。
只此一点误解,好汉们便大错铸成。他们同喝“白开水”的人较量开了,最后一个个如狗熊般趴下来,醉倒在石榴裙下。
我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养成喝慢酒的习惯的,大概总在感到生活太无聊,有太多的时间无可排遣吧。到了这地步我当然被磨平了棱角,使酒也不会任气了。因此心平气和在酒桌一角看过不少好戏。还得出一条经验,常常告诫朋友们说:“切勿和女士斗酒!”
“为什么?”
“女将上阵,必‘有妖法’!”
在同行中,很有些人知道我这句“名言”。
同这样的女士喝酒会肃然起敬和索然无味,就像健美的女将让你欣赏她浑身钢铁般的肌肉一样。
所以我倒是喜欢和普通的(即酒精对她同我一样能起作用)女士在一起喝。她们喝了点酒,会像花朵刚被水喷浇过那般新鲜,甚至像昙花开放时一忽儿一副样子。千姿百态中包孕了一整个世界。
“酒是色媒人”,这句话的解释因人而异。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几杯酒下肚以后,并不就会去干那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勾当。倒是女士们因酒的媒介呈现出来的美丽(常常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这才合那句话的本意。
记得有一次在某地做客,主人夫妇俩来我们这都能喝点儿的一桌相陪。主人先告罪,他不能喝。这就点明是女将出台了。我就静观大家交替同她碰杯。她年轻,亦显得有豪气。我起初以为酒精对她不起作用,看了一阵之后,发觉她并不是喝的“白开水”。她的脸越来越红润姣艳了。眉眼变得水灵又花俏……我看她正到好处,再喝就把美破坏了。正想劝阻,恰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桌面上已是静了下来,大家文雅地坐着,对女主人微微笑。真是满座无恶客,和谐极了。女主人也马上感到了大家的善意,快活得一脸的光彩,把灯光都盖过了。
我总说,美是一种创造,而酒能帮助我们创造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因此美总受到称赞、尊重和保护。当然也有“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恶少,那同酒并没有什么关系。
老天爷没有把饮酒的天才赋给我,因为我是一个男的。
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喝酒的呢?
如果把酒作为触媒剂联系自己的过去,那会引发出许多五光十色的回忆。我想这不光是我,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酒如水银泻地,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它岂止是“色媒人”,甚至是“一切的媒人”呢。
我学喝酒比别人还难一些,我是偷着学的。按老辈的看法,偷着学比冠冕堂皇学效果好得多,说明学习的人有很迫切的上进心。好像饿慌了的人迫切要找点食物填肚皮一样。所以总说偷来的拳头最厉害。可见偷着学喝定然成就超群。
那时候我还是个火头军,母亲做菜时,就派我去灶下烧火。灶角上坐着一把锡酒壶,盛的是老黄酒。烧荤腥时,用它作料。每次只用掉一点儿,所以那壶里经常剩得有许多酒。我烧火的时候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假使我喝红了脸,完全可以说是被灶火烤红的,我何乐而不品尝这“禁果”!不久我母亲就怀疑壶漏了。后来才发现是漏进我嘴里去的。她就骂我“好的不学,专拣坏的学,一点点(北方话叫一丁点儿)的人倒喝酒了!”骂过以后,我就不怕了。因为她没有打我。喝酒毕竟是极普通的事,我们这儿,秋收以后,十有九家都做几斗糯米的酒,后来不知出了多少酒鬼,天也没有塌下来。小孩子早点学会了,未见得不算出息。不过我家因父亲在外地做事,平常无人喝酒,是九家以外的一家。料酒也难得用到,锅子里不是能常烧荤腥的。所以靠那壶也培养不出英才来。我叔父家年年做酒,那只酒缸很大,就放在我们两家的公厅墙角里。叔叔家每年做五斗米酒,半缸都不到。往年我只对做酒的那天有兴趣,因为糯米蒸饭很好吃。如今就对那酒缸有兴趣了。可是舀一碗酒也不容易,我脚下得垫一张板凳,用力掀开沉重的缸盖,把上半个身子都伸到缸里去才舀得到。有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被叔叔碰到。他连连喊着“哎呀、哎呀、哎呀……”一把将我按在缸沿上,掀开缸盖拉我出来。我以为他要打我了。谁知他倒吓白了脸,半晌才回过气来说:“小爷爷,你要酒叫叔叔舀就是了。你怎么够得到!跌进酒缸去没人看见淹死了怎得了!”
难道我还那么小?叔叔总有点夸张吧!
不过那时候我实在并不懂得酒。现在回想起来,酒给我那些乡亲们的影响真够惊心动魄。他们水里来、雨里去。穿着湿透了的衣衫在田里甚至河里熬得嘴唇发紫脸雪白,好容易熬到回家,进了门高喊一声“酒!”便心也暖了,气也顺了。
有些事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一位年富力强的乡亲,虽是农民,却有点文化,若论家中情况,也是“十亩三间,天下难拣”,平时好酒,亦有雅量。可是有一天中午同几位乡亲在一起喝了些,忽然拔脚就走。认准门外七八丈远一个粪池,竟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一纵身,头朝下,脚朝上迅速鱼跃而下。幸亏抢救得快,现在我还非常清楚那时候他像只死猪躺在地上被一桶桶清水冲洗的情景。不管怎么说,就算他喝醉了吧,就算他想寻死吧,就算他平时想死没有勇气,是靠了酒才敢做出来,可是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死法呢?这实在太荒唐。古今中外,自寻短见的人何止千万,死法集锦当亦蔚然可观。但自投粪池,倒还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酒能使人兴奋,思维因此更加活泼而敏捷,如果因而就发展到粪池一跳,则令人瞪目结舌,啼笑皆非了。幸而未死,免得做臭鬼;不幸而未死,这一跳倒使后来的日子不大好过。他自然不愿再提到它,甚至最好不再想到它(可惜做不到)。乡亲们却是通情达理的,况且这一跳虽丑,也不曾害别人,何必同他过不去呢。所以,除了当场亲见的之外,材料并没有扩散出去。我们有个传统,不说两种人的坏处,一种人是酒鬼,一种是皇帝。前者是因为喝多了,糊糊涂涂干出来的坏事,便原谅了他。后者是为了避讳,这可以分成自愿和被迫两种,如果不自愿为长者讳,也要想一想后果而忍一忍,还是多吃饭、少开口好(请看这句谚语造得多巧妙,“多吃饭”的“饭”字换了个“酒”字,就忍不住了)。
不过忍也毕竟不会永久,到后来不就有《隋炀帝艳史》和《清宫秘史》之类的东西问世了吗!
另一位叫人难忘的是我的堂叔,酒神没有任何理由在他身上制造悲剧。因为他非常善良,即使喝醉了也只会笑呵呵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嗜好,我确信他是酒鬼的时候,他已经不大有喝酒的自由了。据说他从前常常在镇上喝了酒醉倒在回家的途中。乡亲们不懂得要如李太白、史湘云那般推崇和欣赏他,反而以酒鬼之名赠之,真是虎落平阳,龙困沙滩,没有办法。尤其是他那位贤妻也就是我的婶娘对此深感厌恶,到年底镇上各酒店来收账时便同丈夫拼死拼活不肯还债,弄得我堂叔无可奈何只得躲开,让债主听他夫人哭命苦,哭她嫁了个败家精男人没有日子过。一直闹到大年夜烧了路头,讨债的人不能再讨下去,才结束了这苦难的一幕。村上人大半都称赞我婶娘守得住家业,管得住丈夫,全不想想我堂叔欠债不还,失去信用,弄得大家瞧不起他,里外都不能做人。他再要上街去赊酒甚至赊肥皂、毛巾等实用品,店主都朝他笑笑说:“叫你老婆来买。”
他还有什么话说呢!他只得沉默,只得悄然从社会里退出来。起初是想说没有用,后来是有话不能说,一直到无话可说,沉默便海一样无底,以至于使得别人都习惯了不同他说话。只有等到秋谷登场,家里做了一点酒,他偶然有机会多喝了几杯之后,脸上才有一点笑意,嘴里才有一点声音。这有多么难得和多么可悲呀!
难道这性格能说是酒铸成的吗!
当然,堂叔的经验别人是难以接受的。我们总不能为了喝得痛快把老婆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吧!
我自己后来有所收敛,则是另有教训。那是在高中毕了业,没考取大学,在家乡晃荡。有位同学邀了个有量的人来陪客。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大约喝了两斤半杜烧酒,睡到床上就不好受了。胸口如一团烈火烧,吐出来的气都烫痛舌头和嘴唇,不禁连连呻吟说比死还难过。后来幸而不死竟活下来了,从此便发誓不喝烧酒。
这一誓言,自然为喝别的酒开了方便之门。
那一次的确是喝白酒喝怕了,誓言是一直遵守下去的。但形势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而我们又必须跟上形势才不致成为顽固派,不致变成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况且即使要做顽固派,也总是顽而不固的。黄酒白酒毕竟一样含酒精,杀馋的功效白酒又比黄酒大得多,人生总不会一帆风顺,面临逆境大都聪明地不会自杀,一旦碰上“有啥吃啥,无啥等着”的局面,他妈的喝酒还管什么是黄是白呢!喝吧喝吧,本来就不存在原则问题。人活在世界上能那么娇嫩吗,真爱护身体就不应该喝酒,既然喝了还装什么腔,作什么势,趁着还有就赶快买吧,谁保证你明天一定喝得上!
真惭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破戒的,就事论事,破戒再喝白酒并不算失大节,问题在于这精神上的反复触动我的羞耻心,认为这无异当了叛徒或做了妓女,灰溜溜地连喝了酒也振作不起来。幸而不久就有了转机,原来酒也是粮食做的,自然也随缺粮而紧张。吃饭难时,喝酒也不容易了。白酒黄酒,我都难得问津了。我的二姨母住在小镇上,从不尝杯中物。有一次我去看她,她竟悄悄拿出一瓶黄酒来,倒一杯叫我喝,挺诚挚地说:“现在买不到别的吃,这酒,也是营养品。”她那音容便使人像得到了极好的宽慰,猛然觉得这苦难的现实仍旧充满了生趣。
“酒是营养品”,姨母的这句话,不但是对我的祝福,也是对所有同好者的祝福。那么就让我们努力去寻觅吧,我们付出了代价,总会有所得。常州天宁寺生产一种药酒,从前叫毛房药酒,不知名出何由,为啥不叫别的,偏叫毛房,什么意思也没有说清楚。现在不可再含糊下去了,否则就是对劳动人民不负责,所以改称“强身酒”。这就同我姨母说的“营养品”庶几近乎哉。常规喝这号酒,早晚两次,每次一小盅,如今难得买到手,又全靠它营养,自然就要多喝些。于是便有人出鼻血,偶然也有牺牲的,可惜当时悲壮的事情太多,喝死了也许有些学不会的人还羡慕呢,况且死者未见得单喝了一种酒,用工业酒精屡了水,难道别人喝过他就能熬住不喝?不过也不能就说屡水的工业酒精不能喝,喝死了他还并没有喝死你们呢。我坦白交代,我在我姨母精神的鼓舞下也喝过,我不是也活过来了吗!所以,我是个活见证,证明前年吴县那个酒厂的生产经验是有前科的,不同的是从前的人耐得苦难,经受得住考验。现在呢,吴县那个酒厂难得生产一批那种酒,竟闹出了好些人命和瞎了好些双眼睛。咦呀,离革命要达到的目标还远得很,现在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么大家就变得这样娇嫩了呢?
毕竟还是不喝酒好,免得误喝了这种要命的东西。
这是局外人的高调,愿喝的照喝不误。其中有些人是看透了,知道要命的东西并不光在酒里边,原是防不胜防的。而另一些人则永远不会喝上这要命东西的,他们的存在,是使过去市场上看不见名牌酒的重要原因。
吴县那个酒厂主生产那种要命的东西,是要别人的命,自己绝不喝。他要喝就会喝名牌酒,用要了别人命的钱去买。
在当前的高消费中,类似上述情形的,我不知道究竟占了多少百分比。
想到这里,不禁忿忿。
忿忿又奈何?总不至因此就禁酒吧!
何以解忧?黄酒一杯……在烟酒价格大开放、大涨价的今天,常州黄酒从四角四分涨到五角一斤,是上升幅度最小而且是全国最便宜的酒类,我一向乐此不倦,所以倒占了便宜,如今还能开怀痛饮。却又怕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过下去,一则今年许多地方的水势,也像物价一样猛涨,淹了不少庄稼。二则人们想发财的大潮,也如黄河之水,从天上奔腾而下,淹没了一切,农肥农药都卖了高价,而且还发现不少是假的。黄酒要用大米做,看今年的光景,真怕又要把酒当营养品了。
从报上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查到假农肥农药后,也责令奸商(这两个字报上还不肯使用,是在下篡改的)赔偿损失。如何赔法没有说,所以我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公平的赔法来。如果仅仅是把钱还给买主,那么我对今后吃饭喝酒都不便乐观了。
所以吃饭难时,千万不要再去学喝酒。学会了想喝,已经没有啦。
不过先富起来了的人倒不必愁,杜酒没有了还有洋酒呢。从前我以为港澳同胞带进来送礼的人头马、白腊克威士忌、金奖马得利是最好的洋酒了。今年去美国待了半年,在许多教授家里都难得看到这种酒,他们平时喝的差远了,因此更肯定了原先的想法。回国时经过香港,在机场第一次看到“XO”每瓶港元四百到一千不等,触目惊心,不知道一小瓶酒为什么那样贵?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因又想起“X0”这个牌子的名称。第一次是在纽约听到的,有位夫人告诉我,她在北京时,邀了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员到她驻北京办事的表兄家做客。这位客人点名要喝“X0”。幸亏她表兄还拿得出。可是这位客人倒了一杯,却只呷了一口就不喝了。真是耍了好大派头。为此这位夫人回到纽约以后还忿忿在念,好像要拿我出气似的。然而她也并没有告诉我“XO”是什么酒,一直到回到祖国以后,才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原来我过去认为的好酒,都还是低档货,只有不同价格的“XO”才独占了中档和高档。
那就喝“XO”吧。
“XO”,这两个符号连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是妙透了,在数学上,“X”是个未知数,“0”是已知数,它们并列在一起,可以看成“X=0”。如果让它们互相斗争,那么“XO”的写法也可理解“X”乘“0”,仍旧等于0。
所以“X0”无论如何也等于0。
那是不是意味着,会把我们喝得精光呢!
这又该是杞人忧天吧,只要看纽约夫人形容的中国作协那个官员,就知道外国人看得那么贵重的东西,中国人还不起眼呢!不光能喝,且能糟蹋。“X0”的值,对中国人等于0,对外国人也等于0。那含义就不一定是把我们喝得精光,也许倒是我们把外国的“X0”喝得精光呢!嘿!
——原文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