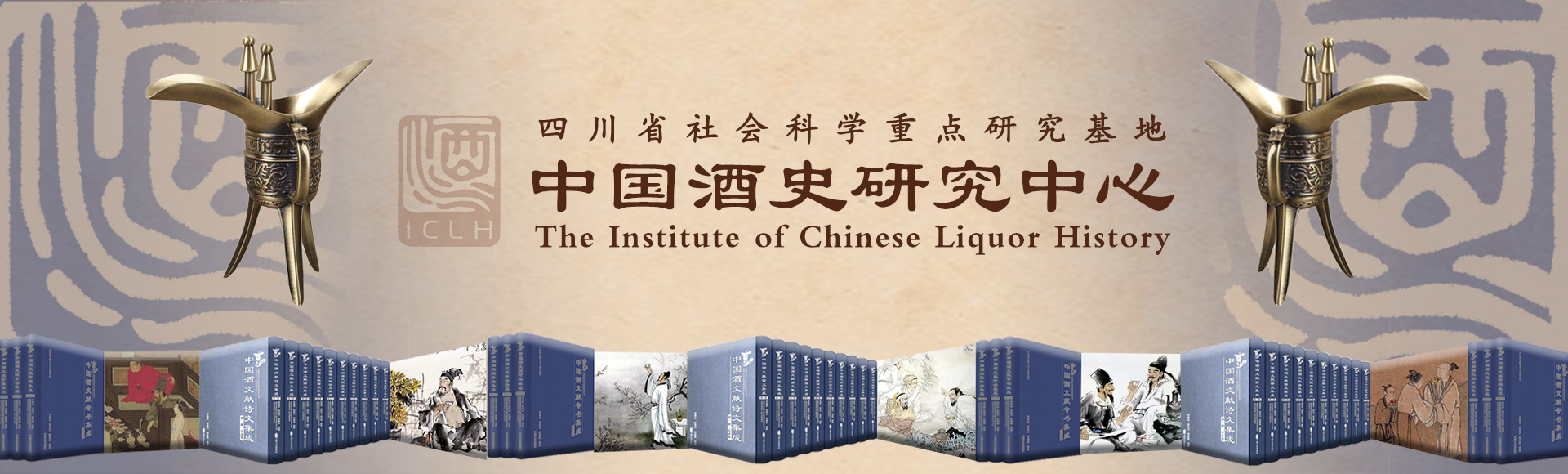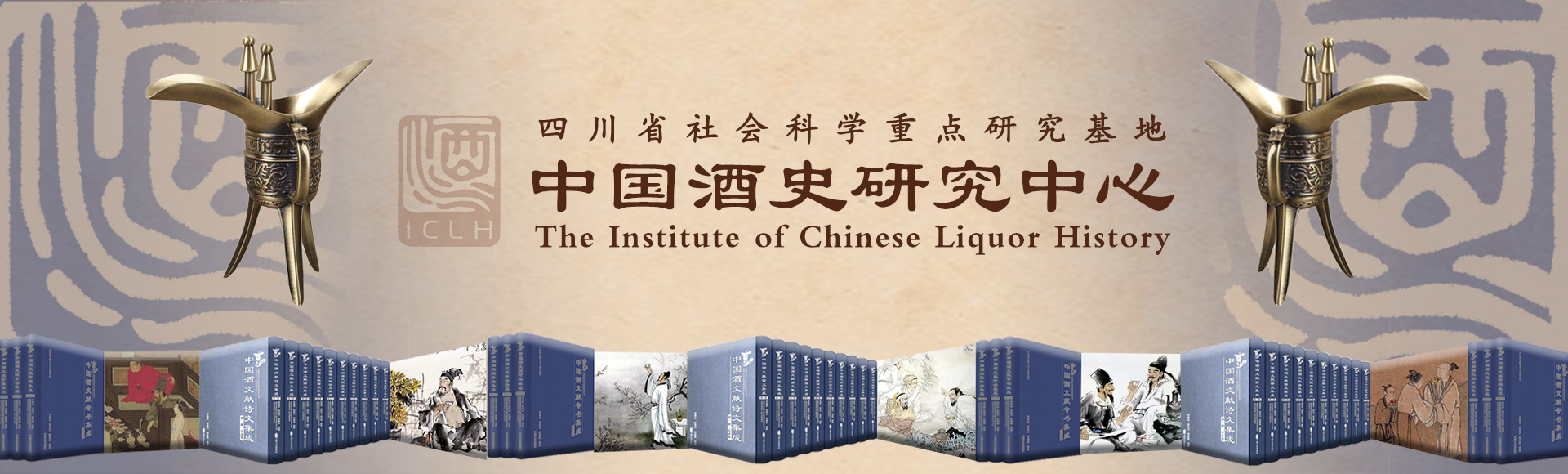这是古典小说《水浒》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的一段故事:“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里来看。……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那李小二,人丛中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这里的“赶碗头脑”,未免使人有“丈二和尚一—摸不着头脑”之感。其实,“头脑”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是不少见的。元代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柴米杂剧》中,小衙内云:“俺两个在此接待老包,不知怎么,则是眼跳。才则喝了几碗投脑酒,压一压胆,慢慢的等他。”这里的“投脑”与“头脑”,是同音异字,一回事也。早在几十年前,“头脑酒”便引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陆澹安(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中说:“我从前以为这种酒早已失传了,最近接到读者郭本堂先生来信告诉我,原来山西太原市至今还有‘头脑酒’。每逢冬令,各饭馆都有出售,把羊肉数块和藕根等放在大碗里,用黄酒掺入。吃的时候,配以类似面包的熟食品,当地叫做‘帽盒子’。初次吃这种酒,很难下咽,习惯之后就喜欢了。”差不多同时,顾肇仓先生在《元人杂剧选》中给“投脑酒”注释曰:“用肉豆脯报切如细麸炒,用极甜酒加葱椒煮食之。”但没有交待这种说法的文献依据。对比之下,陆、顾两位先生所述“头脑酒”的用料,显然有所不同。而且,这是否与元代、明代“头脑酒”相一致,还很难说。从史料记载看来,陆澹安先生曾引明代天启年间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下的记载,即:“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陆先生并说,““头脑酒’见于昔人记载,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一则。”其实,昔人关于“头脑酒”的记载,还见诸明末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七、清初褚人获《坚狐集》卷三等,但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越出朱国桢所述范围。因此,严格说来,当时究竟用的什么肉?什么杂味?什么酒?还是个不很清楚的问题。此外,这种酒为什么叫做“头脑酒”?仍使人费解。近读王仁兴先生的《中国饮食谈古》,引山西民间传说:“在傅山(按:清初著名遗民、医生、思想家)的建议下,这家饭馆起字号为‘清和元’,八珍汤则易名“头脑’。每逢傅山给体弱需要滋补的人看病,便告诉他们去‘吃清和元的头脑’。显而易见,‘吃清和元的头脑’这句听来极其普遍的话语中,蕴含着吃清和元朝统治者的头脑之意。”这种说法,未免牵强附会。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头脑酒”被江南人称做“遮头酒”(《花当阁丛谈》)。遮者,挡也;严冬季节,北京寒气逼人,而每当大风从北方漫卷而至,行人如不戴棉帽、皮帽之类,简直头疼欲裂;而“肉及杂味”、“注热酒”食下的结果,显然可以增加体内热量,特别是能够活血,这就起到了挡风驱寒,以免头痛的作用。可以说,“头脑酒”即保护头脑之酒也。试想,寒凝大地,当您端起热腾腾的“头脑酒”,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啸,甚至欣赏着“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瑞雪,联想着元、明的故实,发一点思古幽情,肯定会其乐也融融的。
至于“头脑汤”,又究系何物?且让我们看一看《金瓶梅》第七十一回的一段描写:“西门庆梳洗毕……须臾拿上粥,围着火盆,四碟齐整小菜,四大碗熬烂下饭,吃了粥,又拿上一盏肉员子,馄饨鸡蛋头脑汤。”看来,这“头脑汤”与“头脑酒”一样,名称奇突。据管窥所及,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头脑汤”的记载,以清代嘉庆年间章杏云著《饮食辩录》卷二所述,最为明确:“馄饨:馄亦作,以小麦面和绿豆粉作薄皮包葱韭或肉渝食,或不用包,切肉菜如糜,和绿豆粉为丸,入汤滴之,其来亦古。唐宋时有肖家馄饨、庾家馄饨,每晨食之,谓之头脑汤,虽无甚益,然汤渝则不热不滞,必无损也。”原来,“头脑汤”就是馄饨,早在唐宋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名称,资格比“头脑酒”更老。这里的“庾家馄饨”云云,可能是“庾家粽子”之误。唐人《西阳杂姐》前集卷七记载:“今衣冠家名食有肖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渝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读此可知也。不过,区区馄饨,为什么又叫“头脑汤”?这仍然是个不解之谜。此谜不妨暂且抛开一边,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慢慢去仔细研究。这里,我想介绍一种明朝人的“馄饨方”:“白面一斤,盐三钱……频入水,拌和为饼剂。少顷,操百遍,摘为小块,捍开,菜豆粉为荐,四边要薄,入馅……用葱白,先以油炒熟,则不荤气。花椒、姜末、杏仁、砂仁酱调和得所,更宜笋菜煤过莱之类,或虾肉、蟹肉,藤花诸鱼肉尤妙。下锅煮时,先用汤搅动,置竹条在汤内,沸,频频洒水,令汤常如鱼津样,滚则不破,其皮坚而滑。”(明高派:《遵生八笺》卷十三)建议有兴趣之美食家,不妨如法炮制,开一家“大明馄饨铺”,很可能会顾客盈门,交口赞誉,名震四方的。
1990年9月24日夜,于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