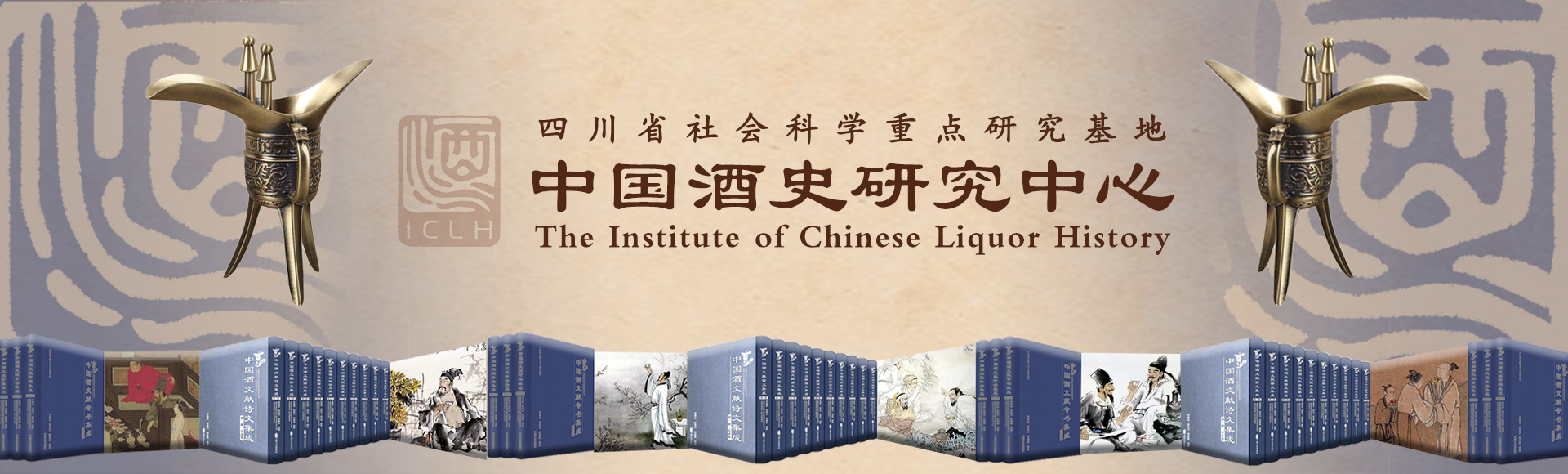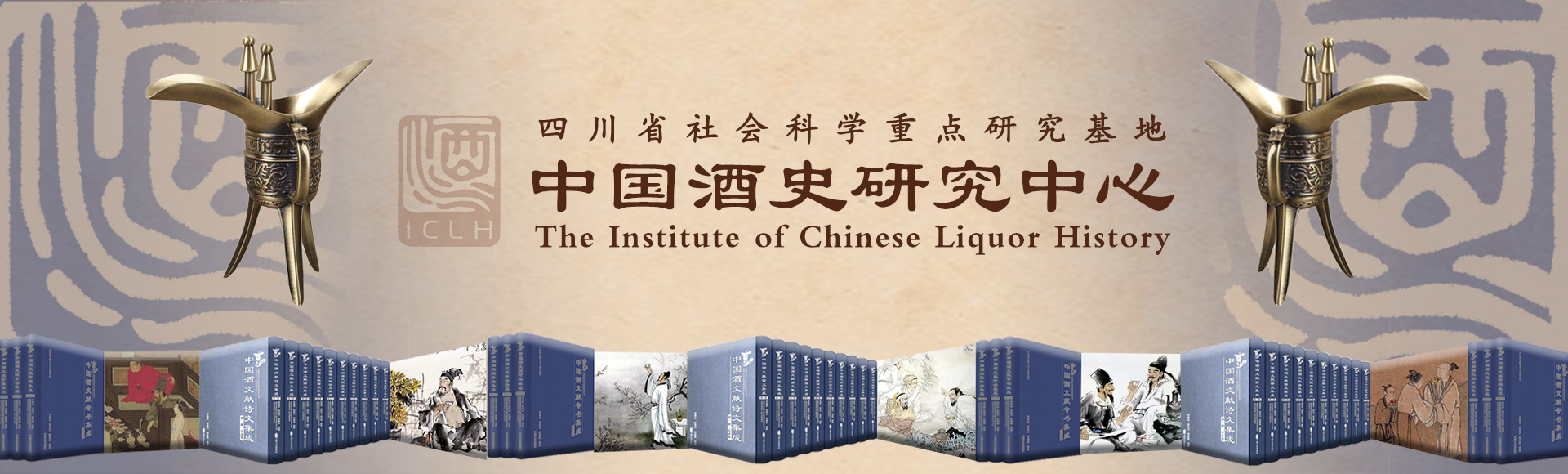一
我不是酒中人,却也积下了不少酒精酒事酒韵,这其中有那么多的汪溢温润心动,也有那么多的号陶苦于无奈。
60年代初叶,也就是那场举世闻名的“大革命”的前夜,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通知我说我将被调往内蒙某旗(即内地的县),为表神圣严肃,通知再三声明,这是组织决定,绝无反复!这于时年26岁、事业爱情正处上升阶段的我不音晴天露雳、天塌地陷,懵懂中我似乎感觉正从云天向地底坠落,坠落……可“组织”是威严的,尽管我满腹话语,想申述想问个究竟,一旦决定下来也只好停止工作,打点行装,准备启行。就在上路的前两天,漫画家方成邀我去他家坐坐。没想到,当我如约去他家时,桌子上已经摆满酒菜,他笑迎我说:
“……老婆上班,孩子上学,中午都不回来。今天就咱们两个,好好喝喝……”
我不禁满身热流,涌到喉头的什么紧堵着,半响说不出一个字。论年龄,他与家父同庚;论成就,他已是当年画界宿将。所以有这份情这份理解,是因为在不久前的“四清”工作队期间,我们曾一起组建了四清工作宣传队,当时他画我写同住一条炕,在两部自制自创的幻灯剧创作中,我们曾那样默契相得、慨然陶然,今后他将继续在画坛驰骋,我则发配边塞不知所终……感于此叹于此,我这从没饮过白酒的黄发小儿也不禁在这位谦谦长者面前举起酒杯,说:
“……我知道您的心意,我喝……”
这以前也曾喝过酒,但从来都是啤酒,与同学与同伴。有时为了赌豪气显气魄,还曾每人抱一升或一瓶,相约不许缓冲只能一气喝干。可与方成,我们饮的是白兰地,尽管这样白酒度较低于中国白酒,乍饮之下,有缕缕醇香,可香味过后,就剩一个辣与呛。我有些不胜酒量,有些晕晕眩眩。
“别急,慢慢来,”方成笑望着我,“酒能助兴,酒能谈心,你就要走了,所以我才……”
“是啊,就要走了,拖着一些未完的事,带着一些未了的情……”
说到这些我不禁眼眶发热心如火焚,随手又举起酒杯,奇怪,这口酒下肚就不再觉辣,而是一身熨帖。
“人生是一条河,一条长长的河。”他也呷了一口,“你这条河刚刚开始流,未来长得很。眼前可能低回蜿蜒,未来也可能遇到激流险滩,可再往后,说不定你要流成一条奔腾澎湃的大河……”
尽管毫无信心,我还是不能不为他的这番祝愿与希冀干杯。于是又喝,他又说了些更切实更慰藉的鼓励与安慰的话。
从他家出来已是下午四点多了,看看满街车流,看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即将赶往发配路的我还是感到人世间的一丝温馨与理解,是那酒的力,还是方成的一腔情?迷濛中我辨不清也不想辨,只口中呐呐道: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二
那年的6月下旬,我背着行李提着箱子来到组织指定的内蒙古的一个边陲小镇陕坝。说它小,倒也有一段“古老”的历史。那就是抗日时期,傅作义将军曾带领所部退守此地,并曾以施放黄河水水淹日本兵,致使日军铁蹄从未踏入此处,至今在陕坝镇杭锦后旗旗委礼堂的匾额处还高悬着“塞上别墅”四个大字。即便如此,这小镇也未改当初的荒寂。可荒寂自有荒寂的好处,是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文革”的烽火已势若狂飚,所到之处,破“四旧”,批斗当权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已经是“摧枯拉朽”处处肃煞;惟这里,“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刚刚学步,其势也就温良得多。白天,学校里也有标语、有口号声;入夜,仍是蛙鸣狗吠,一派僻远的田园状。
我被分配到这里仅有的一家文化单位——旗晋剧团做编剧。说是编剧,在那样的年代也着实无剧可编无剧敢编,只拣选了红极一时的《收租院》改编一下权且上演。转眼到了旧历七月十五,此时,陕坝的白天清爽宜人,人夜,竟有几分寒凉几分清瑟。不知为什么,我这从未沾过白酒的人那天却非常想饮酒。于是找了一只半斤装的空瓶,装满63°的白酒,又买了一把刚上市的小水萝卜、半碗黄酱、两个糖油饼,只等月下独酌。何以只等月下?因为这里的夜着实独具情致。这小镇不在铁路线上,更无高压电线通过。为解决照明和小型工业用电,只好自建一个小小的火力发电站。也是出于自给自足勤俭办事的方针,子夜12时整即停止发电,全镇皆黑。这时,只见星野寂寂,月悬高空,高处,幽冥闪烁;大地,苍苍寂寂,狗吠零落……
待到是夜此时,我的小屋灯光顿逝,皓月清辉渐渐爬满窗棂。看着它的清清与淡淡,不禁酒欲更起,于是边饮边嚼边体味,也便进人无人之境的一个世界。起初,只觉那酒的辣与呛,辣呛中勾起我20多年的人生际遇、生存况味、旧人旧事所爱所愧……回首往事,恍如昨日;看看今天,独坐边城……微醺中我不能不赞美这辣呛的酒的神力,它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它开启了压抑困顿的闸门,它填充了孤独苦闷的空间,它提供了宣泄胸中块垒的天地,它找到了酒韵与情韵的共同旋律……再喝,就觉辣呛之后有了底蕴,因为它能使我对自己说出平时不敢说不便说或说也说不清的话,它也能使我想出平时不敢想不愿想或想也想不透的事。于是不再觉辣,只觉那酒是如此慰帖如此丰饶如此亲切,可不知为什么,待到瓶干底净时我哭了,满脸是泪。泉涌般地,过去读过的关于写酒的诗句纷纷攘攘涌来嘴边,我喃喃着,不知是背给酒听,还是背给自己: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
“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 宜游 宜睡。”
三
光阴荏苒,在内蒙,已呆了7个春秋。那时,我已调到巴盟盟委(即内地的地区)机关报《巴彦淖尔报》做记者,主管文艺版。文革还在继续,但已转向“抓革命,促生产”的阶段。为了体现“促生产”
巴盟最大的牧业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于1973年秋天举行了多年少有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乃蒙古语,即庆幸丰收的意思。许是蒙古族的信仰和习惯,历来的那达慕都是远离城市与乌素(村落),而是选择一块最丰美的草原,一夜之间就搭起帐篷与蒙古包,组成几条商业街组成一座商城,那达慕期间,有市场交易,有商业往还,但更多更显眼的,除了蒙古族崇尚的摔跤、赛马、骑射,就是“跳鬼”。“跳鬼”者,其实酷似化妆舞会,锣鼓喧天中,往往各人化妆成各种鬼怪动物,舞蹈狂欢,庆贺丰收,其状纷纭,其情陶然。“文革”期间,破除迷信,“跳鬼”自然没有,隐遁多年也孕育多年的商业活动、赛马骑射与摔跤却更其狂放,再加内蒙各歌舞团、各种各样乌兰牧骑的演出,倒也气象斐然、隆盛繁华。
一天黄昏,我正边观鉴边采访,忽听见西面传来一阵阵若断若续若隐若现的长调,它们或悠远苍凉,或狂放热烈,随着那清爽劲烈的秋风,朝着那红如火圆如盖的落日,我寻声问迹寻找歌源。穿过错落间,闻那歌声起自一座洁白的蒙古包。我揭帘窥望,不意间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的眼神正与我相撞,他立即起坐迎门:
“啊——老李,请进请进,我们正好对酒当歌。”
美丽其格是著名作曲家,50年代,留学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归国后曾以一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享誉海内外。文革初期以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等罪名被打入“牛棚”,“解放”后,我们曾分别以作曲家、词作家身份汇集呼和浩特共同从事过一段歌曲创作,其间也自然有几次把盏共饮。我知道他的海量,更知道蒙古族的“酒规”——客人到来必须劝酒,方显出主人的热情好客;客人一旦表现出稍有酒量,主人即要尽力敬劝,敬劝不饮即献歌劝酒,歌劝仍不饮,主人即边跪边歌,非把客人饮醉才肯善罢甘休,也才充分表达了主人的热情。有鉴于此,我不得不对他耳语:“我不会喝酒。”
“谁说?”他瞪起眼,“我们喝过。”
“我怕你们的规矩,”说到这儿我不得不使劲捏他的手,“就说我不会,求求你。”
他终于会意,拉着我的手坐于桌首:
“我来介绍,这是北京来的贵客——记者老李。”
话音未落,一位蒙古族姑娘即手托银碗,满满斟上一杯举到我的眼前。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是来看你们饮酒唱歌的。”
“不会也要喝,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姑娘执意不放酒杯。
“这,这……”我不得不向美丽其格求援。
感谢老美的宽容,他终于拔刀相助:“他的确不会。”之后又转向我,“不会也要接酒嘛,少喝些,少喝些。”
我从盘桓而坐到脆地接酒,终于以虔诚的姿态突出困境。
美丽其格一一介绍了在座诸位,与我并排而坐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歌剧团的女导演,面西而坐的是草原上三位男歌手(其中一位已白发飘然),面东而坐的是草原上两位女歌手。他们每人面前摆着一只吃饭用的大白瓷碗,里面斟满了白酒;桌子上摆着热腾腾的奶茶,香味扑鼻的手扒羊,炸得焦黄的油饼、散子,白晶晶的奶酪,炒得硬且脆的黄米……
我说不会喝酒,他们也就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起他们的采歌采风活动,只见他们摆着膀子,边饮边唱。你唱一支,我和一曲,悲凉处涕泪交流,欢快处或击节而歌或以舞助唱。奇怪的是,他们的歌屡唱不尽,他们的喉百唱不哑……看看蒙古包里已经点起蜡烛,我不得不悄悄退出包房。
第二天中午遇到美丽其格,见他仍是睡眼惺松,面带赤红,我问:
“昨晚喝到几点?”
“凌晨四点。”
“喝了多少?”
“你猜。”
我想了想:“一碗就得一斤,三碗到家了吧?”
他晒笑说:“你不了解蒙古人,半天一夜,何止那么些!”
“到底多少?”我实在缺乏想像力。
“11碗!”他用手比比说。
“那不把你烧死?!”
“你别忘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喝茶一边撒尿!”
“噢,原来你有这个绝招!”我正色问,“采了多少风?”
“少说也有200多首民歌。”
“人家说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你是舍不得酒醉采不着风啊!”
他哈哈大笑,颇有“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之美。那达慕大会闭幕时,我为了赶回报社发稿,临时抓了一辆军用吉普乘着夜色疾驰。不知动了哪根筋,巴盟歌舞团团长乌力吉也要搭车而行。他本来喝了太多的酒,却偏要坐在前面与司机并排处。
草原上本没正式的路,朦胧夜色中那路更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军用吉普像撒缰的野马,沟沟坎坎、山包野谷,它一路飞驰如人无人之境。那乌力吉也着实了得,颠簸之中他竟鼾声大作,睡意沉沉,不料,一个大的颠动,他头碰扶手,血流如注,我和司机都慌了。在这前无村后无店的茫茫草原上,何处去包扎伤口?可伤口不包扎,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也就难于设想。还是司机路熟,他看看方位,知道不远处有个公社卫生院,于是径直朝那方向开去,到了那里,一番猛烈的砸门喊人,惟一一位医生才被从床上喊起。他看看伤口,说是裂开的口子很大很深,必须消毒、刮皮、缝合,可眼下没有麻醉剂,病人如何忍受?
“有酒吗?”躺在病床上的乌力吉朗声问。
“草原上的人哪能没酒!”医生不解其意地说。
“这就行,”乌力吉现出一派兴奋,“拿两瓶来。”
医生遵命而行。
乌力吉咬开瓶盖“咕嘟咕嘟”一饮而尽,之后稳稳躺在床上:“开始吧,随便你刮皮随便你缝合。”
“受得了?”医生有点迟疑。
“你要不放心,就把那瓶酒也放在我手边。”
“好的。”医生遵意,麻利地依序而行。待40分钟后,已经缝合完好包扎而毕。
“疼吗?”我问。
“当然有一点,不过迷迷糊糊,一忍也就过去了。”那口气,好像疼在别人身上。
“我看你还是住两天,好些再走。”
“为什么?”
“万一路上再疼,或者有什么危险……”我忧心忡忡。
“怕什么?”他提起那未开启瓶盖的酒,“有了它,我什么都不怕。”
我们只好重新上路。不过这次,我无论如何也把他拉到了后座上。
奇怪的是,到盟府所在地巴彦高勒镇他也没说一声疼,是酒的魔力?还是乌力吉的毅力?至今不得而知。或者真如诗仙李白的诗句: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四
70年代末,随着国运国风的变化,我终于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似乎是否极泰来,几天之间我的命运就起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重返文学界,分得一套三室的公寓楼,一直住在北京爷爷奶奶家的一儿一女也搬到楼上,与妻和我共享天伦,时年39岁的我似乎可以从此安然笔耕养儿育女合家安乐了。不想,时隔一年多,妻即携儿女去美国探亲而且一去不归。他们原本是要我同往的。奈我一因正做文学梦,二想离家多年没聊尽孝敬父母之心,故尔未与同行。悠悠两年之后,妻说为培育儿女不再思归,要我尽快赴美。为人夫为人父的我也就顾不得其他,只能遵意而行。也是为了减少磨折,妻经其在非洲经商的八叔允诺,叫我取道非洲赴美。
在非洲的八叔经营进出口贸易,于西非一带也算声名显赫、资财颇丰。为了居家方便,也为商务应酬,在号称西非的日内瓦——洛美公司所在地还开了一家名“中华楼”的饭店。按照妻的安排,于83年末,我经香港欧洲远赴洛美。未料,因赴美签证的艰难,竟一下困在非洲,做了一年多的海外寓公,真真实实的有家归不得的海外游子。也是平生第一次,我成了时间的富翁苦闷的伴侣无聊无奈的兄弟。
一日黄昏,我正同八叔在饭店前厅同坐,一对白人男女亲亲密密地挽臂而入。八叔立即趋前迎接:
“噢,安东尼!”
他们热情握手。在安东尼介绍了那法国女郎后,八叔也把我介绍给他们。
安东尼的精神分外婴烁欢说,无论如何也要拉八叔和我与他们一起人座,说今天是他远在威尼斯的老母75华诞,为祝贺老母生日,他请客。为不扫他的兴,我们只能遵便。刚刚坐完,他却用法语告诉我们,这位法国女郎是他太太。八叔听罢做了一个夸张的惊讶状,之后转用英语调笑说:
“请问,这是你的第几任太太?”
我为八叔的唐突捏了一把汗。不料,这安东尼却几乎把这带有敏感性忌讳性的问话当成一种夸耀,他夸张地翻了翻眼睛,掐着指头数数说:
“噢,第九位。”
他说的是法语,毫未忌讳。而那法国女郎却为他满满斟了一杯玛梯尼酒送到他的唇边。他一饮而尽,然后热吻那荡然而笑的红唇。我实在不解这两个人的来历,更不解这一男一女对情爱与性爱所持的观念和态度。
可能八叔看出了我的困惑,他乘隙用中文告诉我,那安东尼是一名意大利珠宝商,他不停地穿梭于欧洲、美洲、非洲,他行踪诡秘身上带枪,他赚了大笔的钱也挥霍无度,对女人他朝爱夕改从没有固定的太太;那法国女郎是洛美有名的交际花,她美貌风情谁有钱跟谁厮混……
他们热吻后才正襟危坐,想起为老母的寿诞祝酒。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后我也便找到适当的应酬词句:
“安东尼先生,为令堂大人的祝寿酒已经喝过,我想老夫人的第二件喜事更应该满满地喝一杯。”
“请问第二件喜事是什么?”安东尼望着我。
“为她儿子替她娶了一位美丽、贤良、孝顺的儿媳!”
此话一发,那法国女郎立即狂喜地尖叫一声,她用力吻了一下我的脸颊,即与安东尼同时饮尽杯中酒,然后眨着汪汪泪水的蓝眼睛夸张说:
“李先生真是个天使!”
八叔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喘息稍定说:“他不是天使,倒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作家。”
“难怪他这么善解人意,说得我心里痒痒的。”那法国女郎又要举杯。
我像是鬼使神差,顿时又想起一个凑趣的提议:“且慢,为了高兴,我想再提一个建议。”
“凡是李先生的提议,我一概赞成!”安东尼拍拍法国女郎的背,法国女郎使劲点头。
“今天是三喜临门。一是老夫人75华诞,二是九姨太与安东尼先生新婚之喜,三是鄙人有幸认识二位,宴会又设在中华楼,为尽兴尽欢,我提议下面的酒改饮最有后劲的一种。”“什么酒最有后劲?”安东尼跃跃欲试。
“当然是中国茅台。”
“茅台,茅台?”安东尼眨着他的绿眼睛,“好建议,饮茅台,中国的!”
“那么李先生,请问中国的茅台到底有什么特点?”法国女郎问得虔诚。
酒杯换了中国景德镇的白瓷小杯,每杯都斟满清莹的茅台酒。
“要问特点嘛,请先闻闻它的味道。”
那一男一女果然同时把鼻子凑向酒杯,女士说:“果然芳芬不凡。”
“现在,我们举杯同饮。”
话音落地,我们同时一饮而尽。
“辣,辣!”法国女郎已经辣出眼泪;安东尼也咧起大嘴;八叔则在一旁笑而不语。
“先别喊辣,请诸位闭上嘴。只要你稍闭半分钟,就会感到有一股馥郁的芳香绵绵而生,从舌尖到口腔,随着芳香的扩散通体舒畅,神清气爽…….所以这茅台素有‘风来隔壁千家醉,雨过开瓶十里芳’的美称,所以早在两千多年前,它已经被中国皇帝列为宫中佳酿了…”随着我的解说,这一对男女不断做着尝试,终于安东尼十分折服:
“有劲,的确有后劲,中国酒,厉害!”
法国女郎又饮一杯,神情更加兴奋:
“今天真高兴,我做了一晚的中国皇后!”
“为中国皇后干杯!”
“为中国皇帝干杯!”
“哈……”
“嗬……”
午夜时分,那瓶打开的茅台已所剩无几。安东尼和他的法国女郎相扶相携恋恋难舍地走出中华楼,临行又带了一瓶茅台酒。
在他们,也许正是: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吧?
在我则是:
“三更酒醒残灯在,卧听潇潇雨打篷。”
在这不期而遇的酒席宴上,我似乎谈笑风生且有几分玩世,可内心里却是苦闷的宣泄,无奈与期待的厮拼。那天酒醒后,外面下着非洲独有的瓢泼大雨,“哗哗啦啦”像是天河倒灌,可我在迷漆中似乎真的不知身在何处,又将身归何处?
(作者简介:李硕儒,男,河北丰润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参加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编剧,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晋剧团编剧,内蒙古《巴彦淖尔报》文艺编辑,化工部第十三化建公司宣传干事,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红魔房”之夜》、《爱的奔逃》、《外面的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