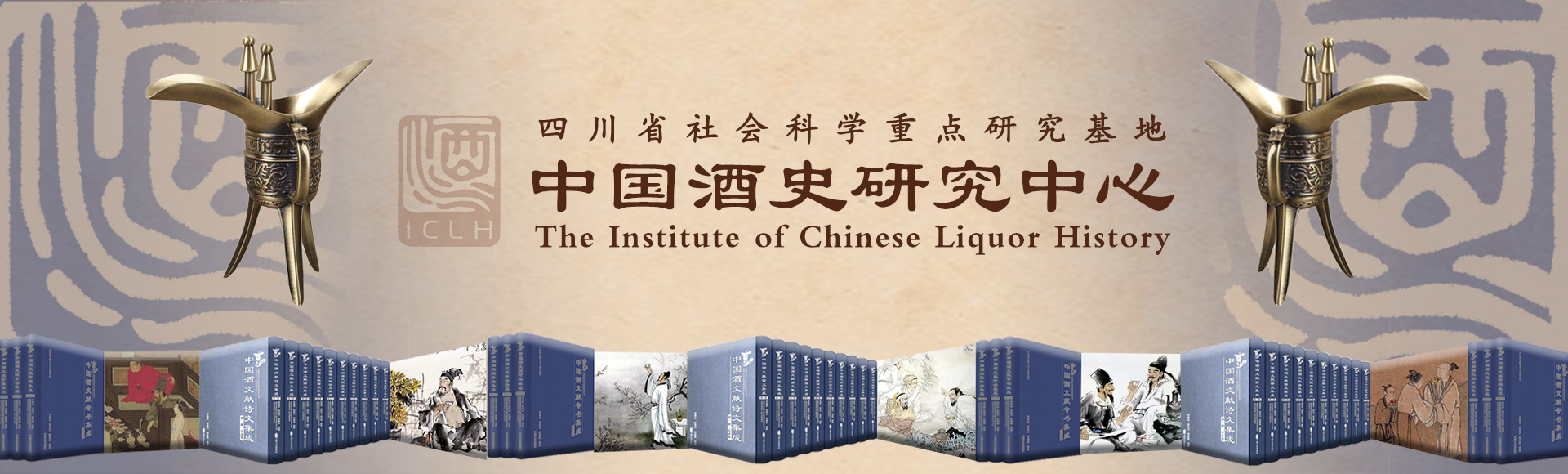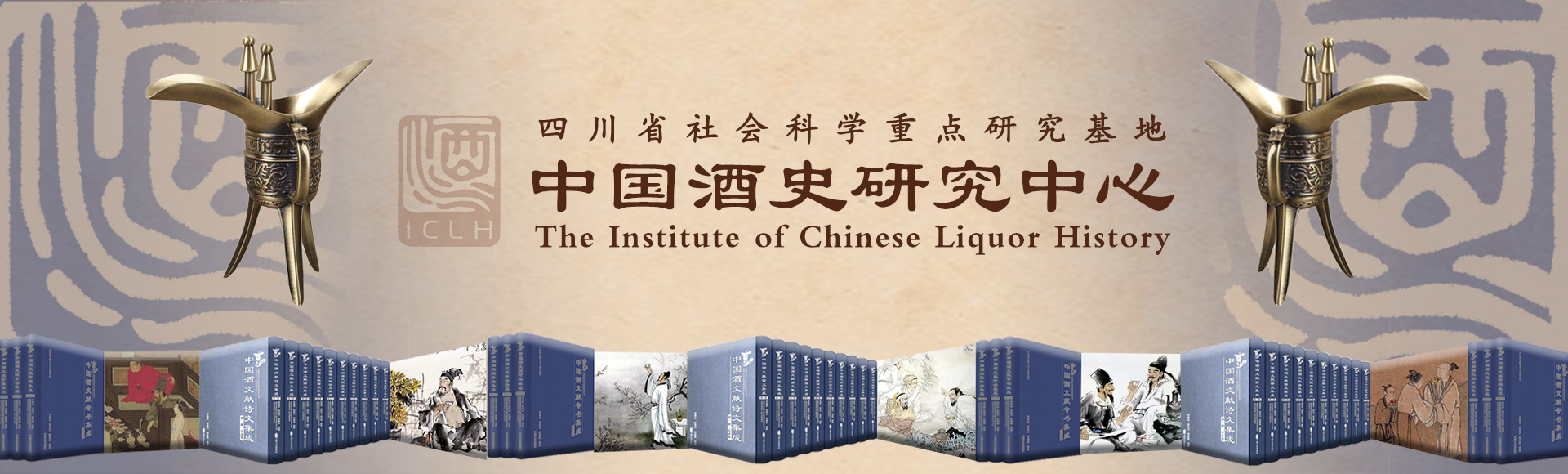岁末天寒,近日气温骤降,唯一的乐趣是靠在床头拥被读唐诗。常念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我忽然渴望身边出现两样东西:雪与酒。酒固伸手可得,而雪,数十年来难得一见,只有从关于合欢山的气象报告中去找。
小时候读这首诗,我只能懂得四分之三,最后一句的味道怎么念也念不出来,后来年事渐长,才靠一壶壶的绍兴高粱慢慢给熏了出来。对于饮酒,我徒拥虚名,谈不上酒量,平时喜欢独酌一两盏,最怕的是轰饮式的闹酒;每饮浅尝即止,微醺是我饮酒的最佳境界。记得陈眉公在《小窗幽记》中特别提到饮酒的适当场合与时机,他说:
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宣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
其实我认为,不论冬饮或夜饮,都宜于大雪纷飞时围炉进行。如一人独酌,可以深思漫想,这是哲学式的饮酒;两人对酌,要以灯下清谈,这是散文式的饮酒。但超过三人以上的群酌,不免会形成闹酒,乃至酗酒,这样就演变为戏剧性的饮酒,热闹是够热闹,总觉得缺乏那么一点情趣。
数年前的寒冬,闻知合欢山大雪,曾计划携带高粱两瓶,狗肉数斤,邀二三酒友上山作竟夕之饮,后因其中一位有事羁绊,未能如期实现,等这位朋友把事情办妥,合欢山的皑皑白雪早已化为滨滨溪流了。计划期间,一位朋友说要带一部唐诗,当酒酣耳热之际,面对窗外满山大雪朗诵,一定能念出另一番情趣来。我则准备带一本《聊斋》,说不定可以邀来一位美丽的女鬼共饮。另一位想得更绝,他说他要带一部《水浒传》。赏雪饮酒与梁山好汉们何干?我们都摸不透他的玄机。你猜他怎么说:当狗肉正熟,酒香四溢时,忽见窗外一位身着破神的大和尚,冒着风雪奔来,待他走近一看,喘!这不正是鲁智深吗?
有人说,好饮两杯的人,都不是俗客,故善饮者多为诗人与豪侠之士。张潮在《幽梦影》一文中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这话说得多么豪气干云!可是这并不能证明,雅俗与否,跟酒有绝对的关系。如说饮者大多为性情中人,倒是不错的。唯侠客与诗人所不同的是,前者志在为世间打抱不平,替天行道,一剑在手风雷动,群魔翘题皆伏首。而诗人多为文弱书生,而感触又深,胸中的块垒只好靠酒去浇了。
诗人好酒,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酒可以渲染气氛,调剂情绪,有助于谈兴,故浪漫倜傥的诗人无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其二,酒可以刺激脑神经,产生灵感,唤起联想。例如二十来岁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他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
《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李白当年奉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也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完成的。当然,这种情况也因人而异,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换到王维或孟浩然,未必就能在醉后还有这么高的创作效率。现代诗人中好饮者颇不乏人,较出名的有纪弦、郑愁予、沙牧、周鼎等人。对他们来说,饮酒与写诗毕竟是两回事,并无直接影响。他们醉后通常喋喋不休,只会制造喧嚣。他们的好诗都是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写成的。至于我自己,虽喜欢喝两杯,但大多适量而止,偶尔喝醉了,头脑便昏昏沉沉,只想睡觉,一觉醒来,经常连腹中原有的诗句都已忘得一干二净。
能饮善饮而又写得一手好诗的,恐怕千古唯青莲居士一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字字都含酒香,如果把他所有写酒的请拿去压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高粱酒来。
李白如此贪杯,他的太太是否也像刘伶妻子一样讨厌酒而强迫丈夫戒酒呢?先说刘伶吧,他的那篇戒酒誓词,的确算得上是千古妙文。据《世说新语》所载:一天刘伶酒瘾发作,向太太索酒,太太一气之下,将所有的酒倒掉,且把酒具全部砸毁,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劝他说:“你饮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须戒掉。”
刘伶说:“好吧,不过要我自己戒是戒不掉的,只有祝告神灵后再戒。”他太太信以为真,便遵嘱为他准备了酒肉。于是刘伶跪下来发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祝祷既毕,便大口喝酒,大块进肉,醉得人事不知。这种妇人,也只有刘伶这种办法来对付。李白的太太是否也干预他的酒事呢?遍查史籍,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不过,倒可以在他的《将进酒》一诗中得到一点暗示:最后他为了“与尔同销万古愁”,不是很兴奋地命儿子把名贵的五花马、千金裘拿去换酒吗?假如他事先未征得太太的同意,他未必敢如此慷慨。由此足证,他的太太当不至像刘伶妻子那么泼悍,凡事还可以商量的。
在这方面,苏东坡的太太就显得贤慧多了。《后赤壁赋》中有一段关于饮酒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供天下诗人的太太参考。话说宋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某夜,苏东坡从雪堂步行回临皋,有两位朋友陪他散步而去,这时月色皎洁,情绪颇佳,走着走着,他忽然叹息说:
“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宵何?”
一位朋友接道:“今者薄暮,举纲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有鱼就好办,于是苏东坡匆匆赶回去跟老妻商量。苏夫人果然是一位贤德之妇,她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只要听到这两句话就够醉人的了;这个女人不但是一位好主妇,也可以说是苏东坡的知己。
金圣叹的《三十三不亦快哉》中,也有一则提到向太太索酒的事:一位十年不见的老友薄暮来访,一见面不先问他坐船来或是搭车来,也没有说请坐,便直奔内室,低声下气地问太太:“君岂有酒如东坡妇乎?”金太太虽不像苏夫人经常为丈夫藏好酒,但毫不考虑地从头上拔下金簪去换钱沾酒,这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妻子。
比较说来,西洋人比中国人更好酒贪杯,成年后的男人几乎人人都能喝酒。也许正因为饮酒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普遍经验,故很少成为诗的题材;西洋诗中有不少描写色情的诗,却罕闻酒香。反之,由于中国古典诗中关于友叙、送别与感怀这一类的作品最多,故诗中经常流着两种液体,一是眼泪,一是酒。泪的味道既咸且苦,酒的味道又辛又辣,真是五味俱全,难怪某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是纯感性的。如何在创作时保持高度的清醒,在作品中少掺点眼泪和酒,以求取感性与知性的均衡发展,这恐怕是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应该三思的。
(选自《一朵午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