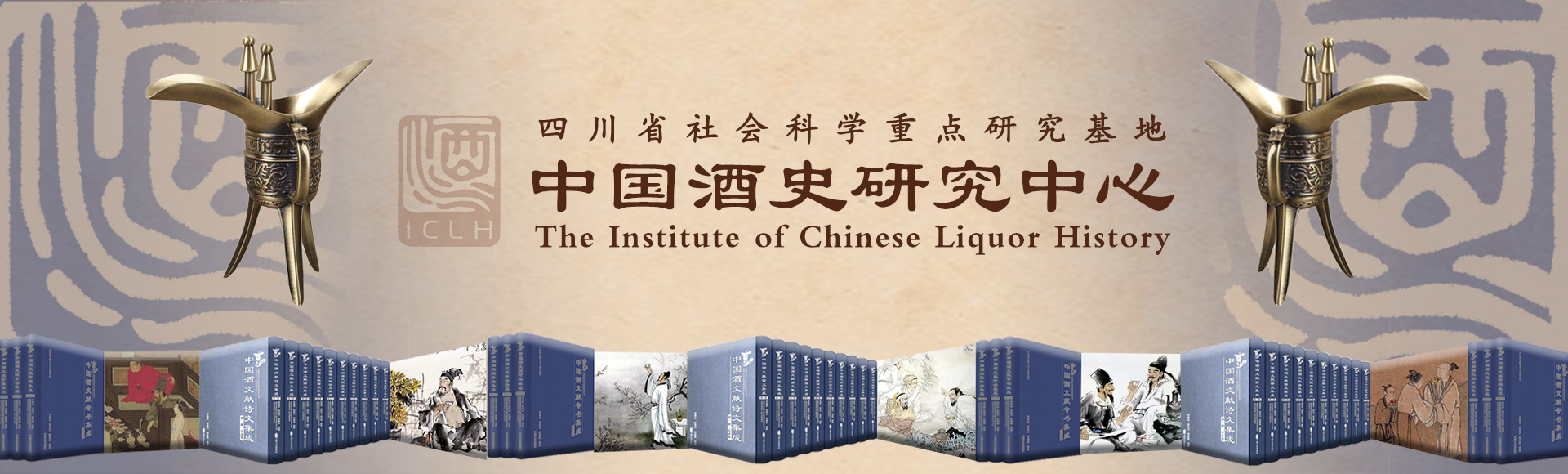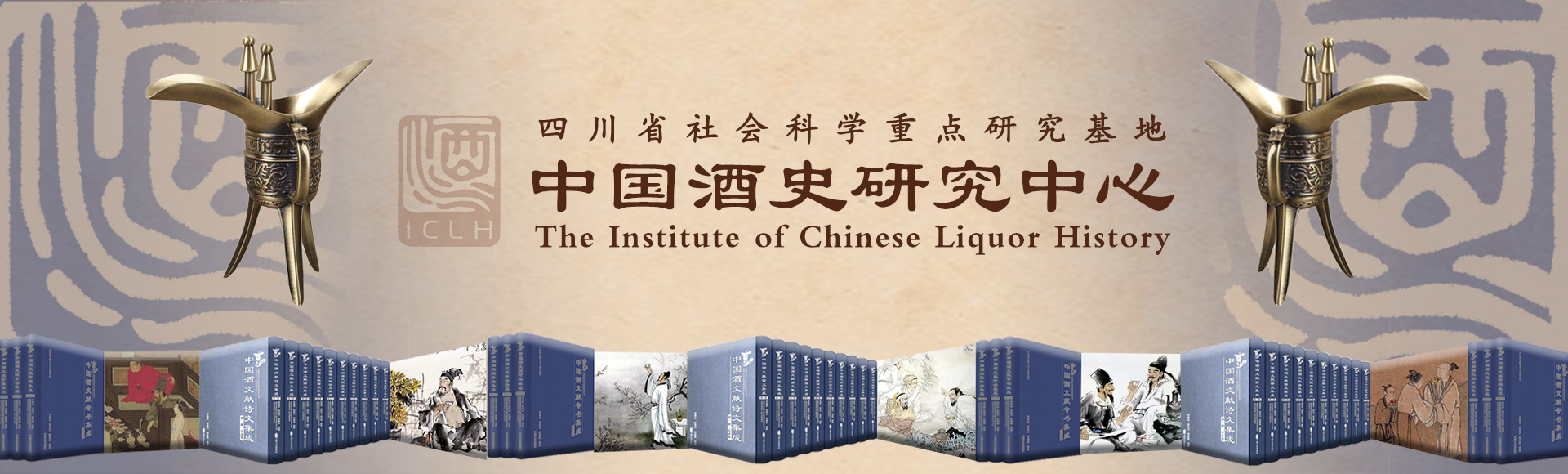苗子曰:君友杨宪益,沉酒曲柴,嗜威士忌如命,而赐之以佳名日“苏格兰茶”,盖讳言酒也。吾未敢以直谏尽友道,因集古酒人荒诞之事以进之,题曰《酒故》,纪故实也。宪益阅此,殆会心笑,而嗤之日:老头不可教也!
小时候读书,对禹很崇拜。书上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觉得这样一位古代贤君圣主(虽然顾颉刚先生的考证,说禹只不过是一条“毛毛虫”),果然善于克制自己的嗜好而爱听群众的有益舆论。近来年纪大了,对于事物总爱动动脑筋,这才知道小时候相信这句话是上了儒家的当!你看,禹的生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年,即距今四千年前,距新石器时期的氏族社会还很近,那时的酒,只是烂野果或各类植物泡在水里发酵造成的,顶多像今天的甜酒,含酒精量不多,绝比不上大曲、茅台、五粮液……根本谈不上“旨”。喝点果酒,醉不了人,他老人家就不高兴了。
《说文》说:“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说明禹这个人伪善。“禹闻善言则拜。”(《孟子》)“拜”,用今天的话,等于说,“您提的意见已看过,十分宝贵”,夸奖过“宝贵意见”,“拜”
了,只是并不实行之,这正是官僚主义的典型。何况仪狄做的既然是“美酒”,这就可以出口赚外汇,国家酒税收入也可大大增加。从经济价值来衡量,仪狄先生实在是一位科技生产的开拓者,如果禹不“疏”他,那么不要说威土忌、白兰地……之类用外汇买的饮料可以不必从外国进口,最低限度“可口可乐”那种不醉人的甜饮料,也可以不需引进设厂了。一方面赚外汇,一方面节省国家外汇支出,“旨酒”肯定不是什么可“恶”的!想通之后,鄙人对禹就不那么崇拜了。
读过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人,约略知道“诸贤”的饮酒服药,其中有点“避世”之意,但也不尽然。当时有两个大酒鬼——嵇康和阮籍。嵇康同曹操的后代有裙带关系,官拜中散大夫,后来司马氏取代了曹氏家族,嵇康失去了靠山,只好回家当铁匠,图个出身好的工人阶级,以为这就没事了。但是依旧逃不过汉奸钟会的手掌,嵇康夏月常锻大柳下,钟会过之,康锻如故,“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晋书》)双方针锋相对地口舌一场,钟会便借故杀了嵇康,他临死只遗憾所弹的《广陵散》没有传给后代。阮籍这家伙比嵇康“鬼”得多,稀康喝酒只是喝酒,没有借酒来搞什么名堂,阮籍却不然,“司马昭(晋文帝)初欲为子炎求婚于籍,籍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欲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小说上有“借水逝”之法,他老兄却发明了借“酒”遁,不想把女儿嫁给高干子弟(后来还当上了相当于国家主席的“晋文帝”),就借酒装醉。对付野心勃勃的对立面,也借
“酣醉”的办法得免于“罪”。>司马昭用他做“大将军”、“从事中郎”,他为了不想太靠近权贵,以免猴年卯月“咔嚓”一声丢了脑袋不太好玩,就借口警卫部队步兵炊事班会酿酒,还存下了三百解酒,就要求当步兵校尉这个“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奥服光丽,伎巧必给”(《通典》)的武散官,乐得个逍遥自在。阮籍终于不像嵇康那样傻,白白地给奸雄钟会“咔嚓一刀”。
阮籍他们那一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中说道:“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陈平、曹参以来,俱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项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酒者耶?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这种“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的权术,恐怕不是酒徒所认同的。不过我们北面的邻居,据说不久前也有很多酗酒的居民,他们也常常“以酒杜人”。可惜他们吃醉了经常回家打老婆,家庭矛盾超过政治矛盾。
钟会这厮,从小就暴露出他那肆无忌惮的性格:有一天,趁他爹午睡,他和哥哥钟毓就一起去偷酒喝。老爹钟舔其实没睡着,就偷看他们的举动。钟毓端了酒,作了揖后才去饮,钟会舀起了酒就喝,没有作揖。钟舔起来问钟统,为啥作个揖才喝酒,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问到钟会,他干脆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魏略》)是啊,那些滥用公款饱入私囊的人还恭恭敬敬地向国库作个揖,这才是头等“傻帽”呢!
钟会后来终于反了司马昭,最后被乱军杀了。
和嵇、阮同属“竹林七贤”的另一个大酒鬼刘伶,也是酒界中知名度很高的前辈。那时候的人,可是不太讲精神文明,刘伶喝醉了,就“脱衣裸形屋中”。虽然那时《花花公子》之类的刊物尚未出版,他也算得当今“天体运动”和“脱星”的老祖宗了。有人责怪这醉鬼太放肆了,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居室,把房子当裤权,是你们自己跑进我的裤衩当中去,你怎么反怪我呢?”(《晋纪》)这句话在入世的哲学家看来,是彻底的荒谬的主观唯心论,但文学家会欣赏他的浪漫主义意念,认为没有这种荒诞的意念,文学是不会产生的(虽然他生平“未尝厝意文翰”,一辈子只写过一篇《酒德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且由它去吧。人类都喜爱外形美和勇敢品德,可是史书上却说刘伶“容貌甚陋”。他曾经和人争吵,别人抢起拳头就要揍他一顿,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站起来慢慢地说:“鸡肋何足以当尊拳。”那人也确实觉得不值得打那么一个“孬种”,于是这场本来极其壮观的超级武打,就告终了。不要以为凡是酒人都是武二一般好汉,即使自认为“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的刘伯伦,在现实生活面前,其实也不过是自认虫的阿Q之前辈云耳。
刘伶当过建威参军这不大不小的官,“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似乎对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随便,但是从他在拳头面前的那副熊样,很可能鹿车上受点风寒,也得马上赶回家去喝板蓝根和速效感冒片。他这句话说得倒通达,可比起三国时代的郑泉,却差得远了。郑泉这个醉猫,临终前告诉他的朋友说:“必葬我陶家(注:做陶器的人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为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吴志》)郑泉的遗嘱,希望骨灰变成泥巴,让百年之后制陶的人把它捏成一个酒壶,这才不愧是个真正的酒汉!如果我的朋友—
工艺美术家韩美林捏的某一个酒壶确实用的是郑泉骨灰的料,那么,我一定向他讨来转赠给杨宪益兄。不过世界上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保不定百年之后,陶家挖了郑泉的骨灰,却捏了个尿壶……
《遁斋闲览》有一段故事:“郭朏有才学而轻脱。夜出,为醉人所诬。太守问,删笑曰:‘张公吃酒李公醉者,腊是也。’太守因令作《张公吃酒李公醉赋》,朏爱笔曰:‘事有不可测,人当防未然。清河文人,方肆杯盘之乐;陇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意………守笑而释之。”“张公吃酒李公醉”,是古时候一句俗话。郭朏好端端被人诬告他喝醉闯祸,当然是无妄之灾,幸好这太守也是个书呆子,叫他做一篇赋就放走了。大革文化命的年头,被诬的很多,你越是掉书袋,越是引用经典著作据理力争,你就越倒霉。毕竟玩养政治的像这位太守那样的人少。至于郭朏那首《张公吃酒李公醉赋》的开头两句,倒是耐人寻味的。
自古及今,似乎诗和酒的关系特别亲切,以酒为题材的诗,真是罄竹难书。陶渊明是较早的一位酒诗人,李白更不必说。据郭老的考证,杜甫也是个酒鬼(当然,他的《酒中八仙歌》不会把他自己写进去)。我倒是喜欢白居易的《劝酒》:
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梅酒!
地球永远转动,人的寿命短促,把短促的寿命浪费在钞票追求上,“身后堆金拄北斗”图个啥?!我近来虽然一点酒都不沾唇,但“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的酒徒心情,却是能了解的。
这里还是用姓杨的故事作结束:宋初有个老头叫杨朴(据说近来的文艺家都喜欢这个祖宗,我没有考证过他是宪益的第几代祖宗,也不知道他认不认),是个怪人,平日骑头驴子在郊外溜达,然后躺在草窝里作诗,“得句即跃而出”,把过路人吓一跳。宋太宗、真宗都召见过他。《候鳍录》有一段记载,“宋真宗征处士杨朴至,问曰:‘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诗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草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从前的知识分子不愿当干部,害怕什么时候闹个把运动,老头皮便“咔嚓一声”保不住。现代的知识分子受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知道做官是“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于是很多人都愿意,并且实践过“捉将官里去”的光荣。不过贪酒咏诗,是否都戒了,在这里却各人都还有他的自由的。
(选自《解忧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