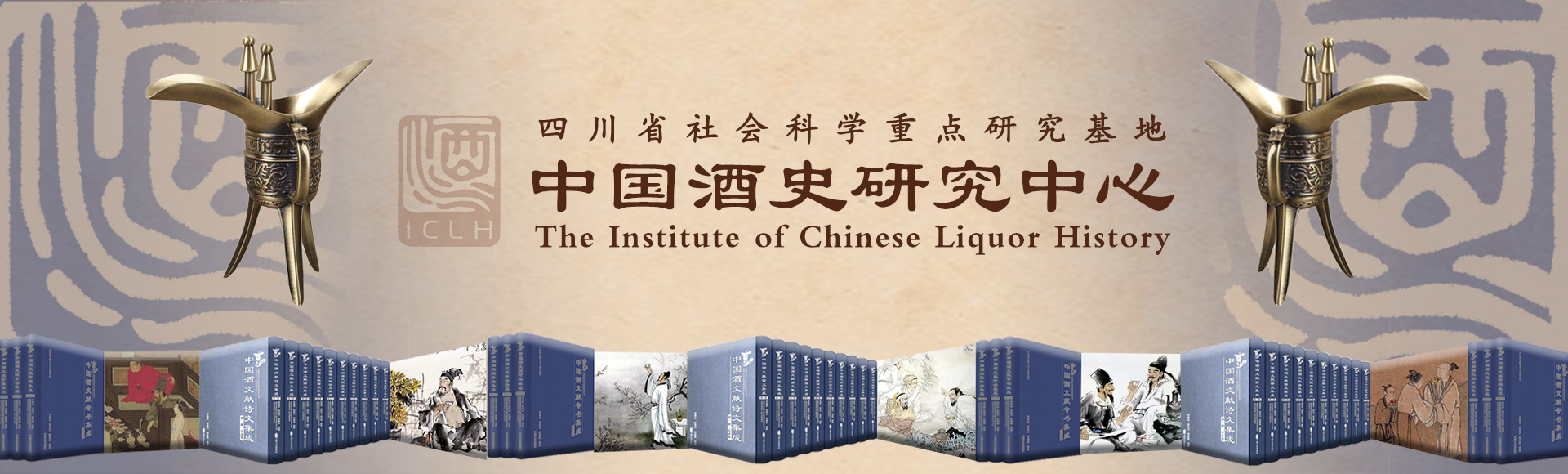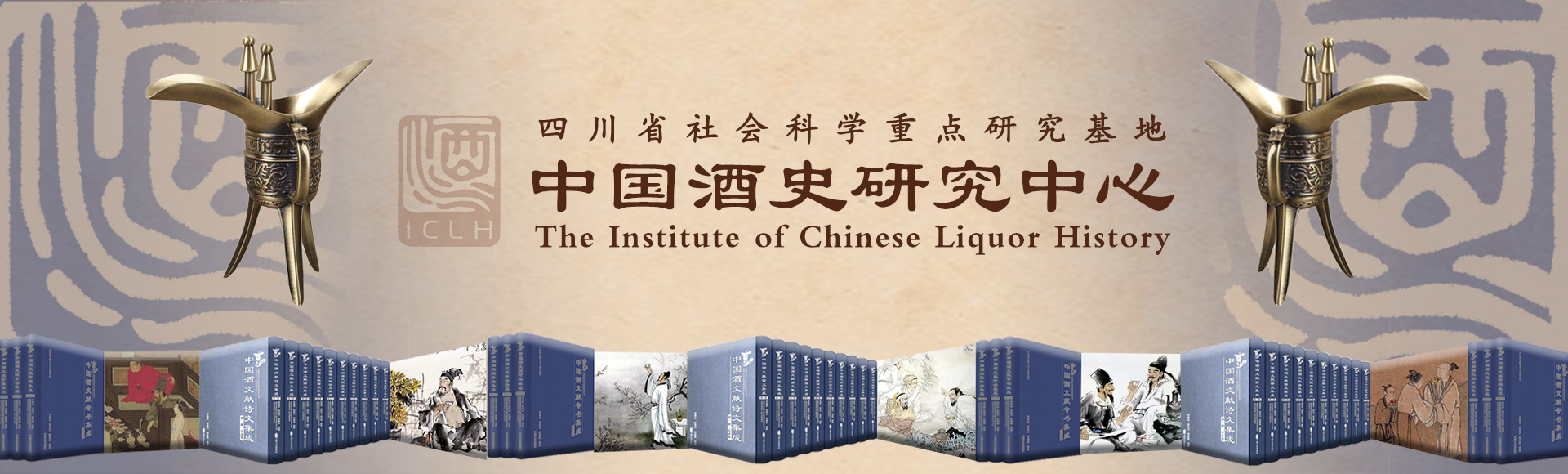摘要:味觉思想之确立,原本作为欲望表达的饮酒被转换为认知方式与思想方法。苏轼、朱肱等人进而从味开始考察酒,追寻酒趣、酒德。尤其从性道之维领会酒,深刻阐发了“以酒为命”“酒近于道”“酒中有妙理”等精义,揭示了酒的形上内涵。自此,对于士人来说,饮酒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它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性命、道理的展开,更是自觉的精神修行。饮酒敞开酒中之道与理,以及人自身的性和命,酒也就由外在的欲望对象转换成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当饮酒被当作形上活动,日用常行也就有了形上意义,这些洞见无疑为“日用即道”观念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关键词:酒文化;苏轼;朱肱;酒近于道
远古以来,酒以其甘美之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饮酒使人快乐,故有“酒为欢伯”之称。换言之,酒乃口腹之欲的对象。因为被当作欲望,所以也被人们提防,“以礼饮酒”可以看作对作为欲望活动——饮酒的自觉规训。魏晋时期,随着味觉思想的确立,饮酒超越欲望,逐渐被士人当作思想方法。魏晋人醉的自觉正基于此。“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光禄)“酒正引人着胜地”(王右军)“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佛大),酒被理解为“使人人自远”“引人着胜地”的方式以及“形神复相亲”的方法。这些高妙的境界或人生体验借助于酒才能实现。陶渊明“对酒绝尘想”与李白“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表述中,酒也被当作超越尘想与通达大道的基本方式。在他们表述中,酒本身有何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酒能够让饮者达到思想目标,正是在此意义上,酒获得了思想方法的意义。
宋儒以“乐”对抗“苦”,他们一改魏晋隋唐以酒对抗尘俗、对抗人生之苦的做法,不再把饮酒当作通达思想目标的工具。“深深酒不为愁倾。”“太平自庆无他事,有酒时时三五杯。”“愁”“苦”不再是饮酒之因,“与愁对”反倒降低了酒的价值。饮者不必为酒之外的目的而饮,也不是因为酒能够把人带到他处才饮,饮酒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
随着酒在民间普及,饮酒在北宋被当作人情之常。相应地,人们对酒的领悟大大深化,开始对酿酒技术及酒的精神品性进行系统理论总结。就理论水准看,苏轼的《浊醪有妙理赋》与朱肱的《酒经》之“总论”最有深度。他们都认识到酒中有“理”,有“道”都贯彻从“味”开始路线,又都由酒显道。在酒与人关系上,他们都坚持“以酒为命”说,自觉追求“酒中之趣”。他们试图从心性与道两个层次理解与规定酒,从而赋予酒以深沉的形上内涵。
……(略,详见附件)
饮酒不仅通大道,酒本身即近于道;饮酒不仅合自然,人愈醉愈自然;饮酒不仅使形神相亲,醉本身就是生命的大和谐。“以酒为命”,饮酒就是在增强自己的生命,包括增强自己的精神生命;“酒中有理”,饮酒就是以理净身的工夫,身与理合而如理而在;饮酒就是“穷理”。“酒近于道”,饮酒则可使身与道合,与道为一。不妨说,一场酒就是一场精神修行,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
酒中有道,有妙理。人饮酒而使酒成为人的内在精神生命的有机部分,亦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根据。较之把酒认作口腹之欲的对象以及将酒单纯当作工具性的思想方法,宋儒承认酒具有独立自足的精神价值,自觉把酒拔高到性道层面,这大大深化了对酒的认识。宋明以来,饮酒逐渐由人情之常转变为日用之需。当饮酒被当作形上活动,日用常行也就有了形上意义。这些洞见无疑为明儒“日用即道”观念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正是基于酒具有性道价值,人才得以在饮酒中过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