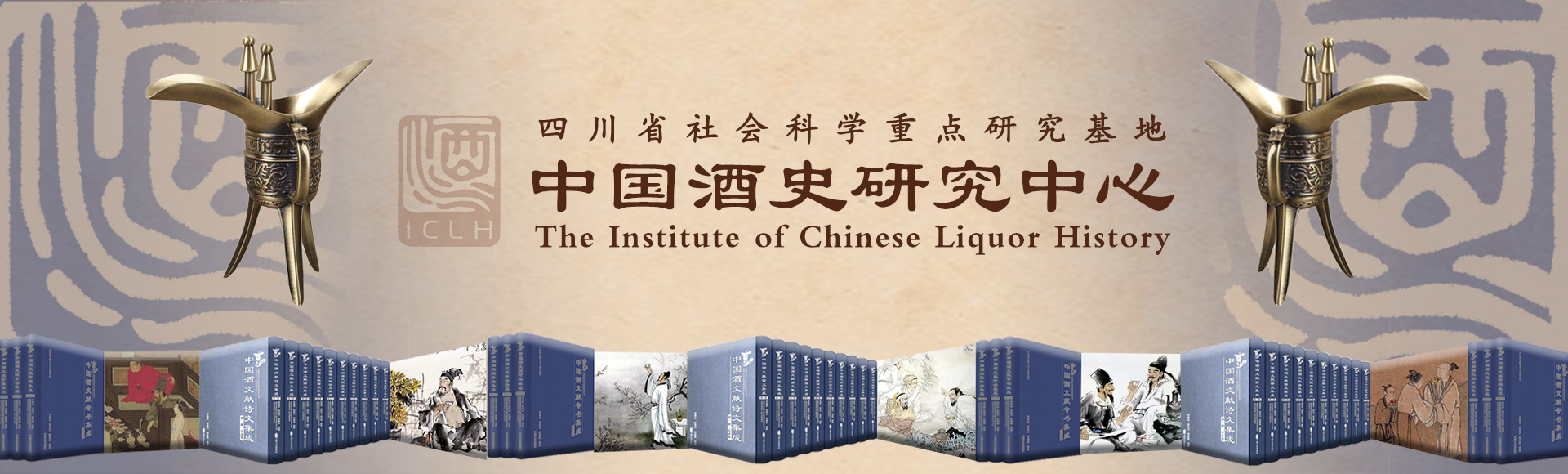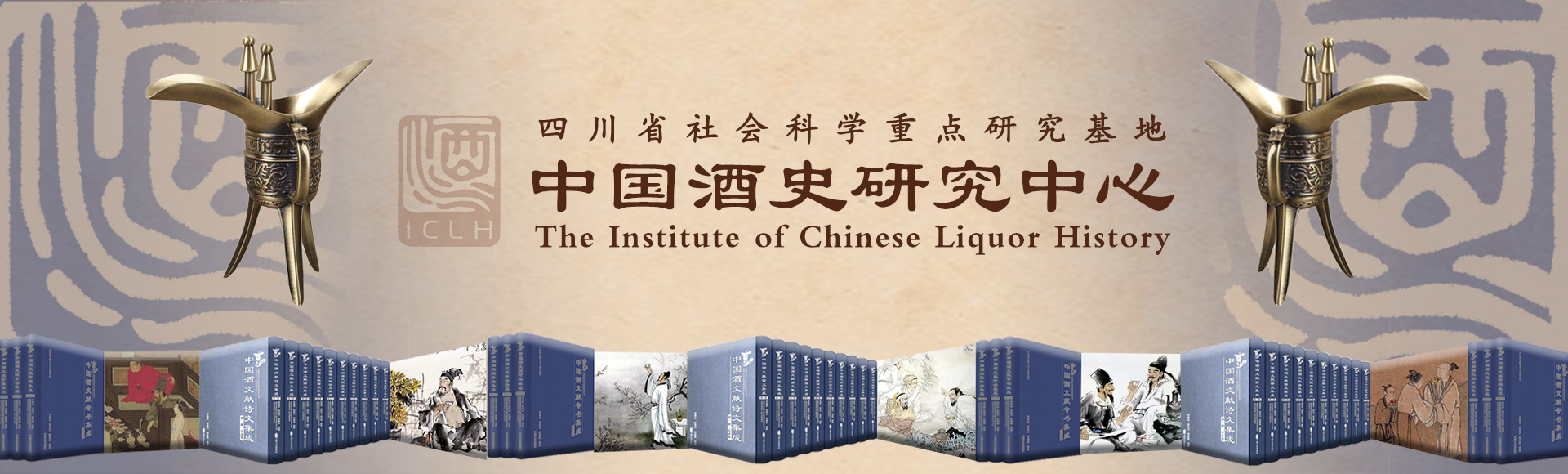西汉海昏侯国酒俗文化考略
——以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筵席器具为例
刘爱华
作者简介:刘爱华,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俗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摘要: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筵席器具,反映了西汉上层贵族雅致的饮食文化,而“酒”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主要体现在:一是造酒的酒器,如大型青铜蒸馏器,其结构完整复杂,体型硕大,包括天锅、地锅、导引管和馏口,反映了西汉比较成熟的酿酒工艺;二是储酒的酒具,如龙盘凤碗、耳杯、樽、卮等漆器,玉耳杯等玉器,还有青铜钫、青铜缶、青铜壶等青铜器,尤其是凤纹提梁,凸显了主人的尊贵身份;三是佐酒的酒具,如体现西汉分食制的染炉、席镇、温鼎以及雅乐活动的整套铁编馨、琴、瑟、排箫等乐器,较完整地反映了西汉贵族社会的佐酒之礼,举手投足、行卧坐立乃至赏乐均应“不逾矩”,遵守宴饮俗制。这批珍贵的筵席器具,以“酒”为媒,突出地展示了西汉酒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生动地勾勒出西汉上层贵族社会的民俗生活图谱。
关键词:南昌;海昏侯墓;筵席器具;酒俗
海昏侯墓及其发掘成果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为历史学、民俗学、博物馆学、艺术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展深入研究,全面了解、研究西汉社会尤其是区域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文献佐证。海昏文化研究是一个宏大课题,仅出土文物的解读就是一个巨大工程,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提梁卣、铜“火锅”、染炉等筵席器具及遗留的虫草等实物,较完整地勾勒出了西汉上层贵族雅致的食俗文化,而“酒”又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本文依托出土文物,从酿酒、储酒和佐酒等三个方面对西汉上层贵族酒俗文化进行管窥,以求教于方家。
一、造酒:极富想象的酿酒器
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青铜蒸馏器,包括天锅和地锅两个部分。考古专家认为汉代墓葬中这种蒸馏器的发现非常罕见,且体型庞大、结构完整,可能与酿造低烈度白酒有关。假如这个推测得到验证,意味着我国白酒酿造史将大大提前。
中国白酒从什么时候开始酿造,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学界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说法是成熟的白酒生产应该在元朝,忽思慧《饮膳正要》载:“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
“阿刺吉”是阿拉伯语音译,是“汗”“出汗”的意思,描述蒸馏时蒸汽在容器壁上凝结成汗状。后来学者考证,这种“阿刺吉”酒就是蒸馏出来的烧酒。这种说法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得到佐证,“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当然最有力的证明则是江西省进贤县李渡镇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发现了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等遗迹。这一考古发掘有力地证实了在元代白酒生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白酒酿造是否始于元代呢?从考古资料来看,肯定要早于元代,至于究竟源于何时,目前学界并无一致的看法,存在东汉说、唐代说、宋代说等多种说法。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型青铜蒸馏器是否为酿造白酒的蒸馏器,学界也无统一意见,有待于更多考古发掘资料予以证实。当然,笔者偏向认为它是与低烈度白酒酿造有关的蒸馏器,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这套器具结构复杂、完整,有天锅、地锅、导引管和馏口,至少是一种蒸馏器具;第二,这套器具在海昏侯墓酒具库中出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能和酒有关;第三,该器具出土时其内的残留物经过科学鉴定为芋头。芋头属于薯类,薯类是制作白酒的常见原料之一。芋头在日本曾经被用来酿造过低烈度白酒。在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编的《酒水知识与服务》教材中,在酒的分类一节中提到一种叫“俄克莱豪(Okolehao)”的酒,“该酒是夏威夷的特产酒,是以芋头(当地称之为Ti)为原料而制成的蒸馏酒,简称为欧凯(Oke)。夏威夷的当地人一般都直接饮用,但更流行的饮用方式是在俄克莱豪酒中兑入可乐或橙汁一起饮用”。在我国,这种芋头酒的制作工艺,也已申请了相关发明专利。学者已有初步研究,并且这种酒仍然盛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成为当地招待贵宾的特产。
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透露,蒸馏器中残留物含有芋头,可能与日本清酒的酿造有类似的工艺。“根据日本的酿酒史,直到现在,日本还是用芋头来酿造低度的白酒,也就是清酒。日本的标准清酒就是用芋头来造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是不是引进了我们的酿酒方法,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了,现在不能完全确定。”据了解,日本烧酒(烧耐)是用其独特的蒸馏法制成的,制酒材料就包括芋头、红薯、大米等。台湾生产的甘薯与芋头的质量均佳,适合供作蒸馏酒之原料,但却没有日本那样的蒸馏酒。海昏侯墓青铜蒸馏器中还发现了板栗、荸荠、菱角、花生等,这些可能也是果酒的原料。因此,综合以上三个原因,笔者认为该蒸馏器与低烈度白酒酿造有关,或者至少与果酒蒸馏技术有关。
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熬药的工具。笔者觉得这个更加不可信:一是熬药要满足煮的需要,结构相对简单,口沿应该有便于手持的双耳之类。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双耳铜钱数件,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其是熬药器。而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没有双耳。二是熬药器需要一套配套的器具,如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匙等,这些在海昏侯墓酒具库中并没有发现。因此,该蒸馏器显然不是古代熬药器。
当然,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大型蒸馏器是否与低烈度白酒有关,还有待于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酿酒器具。西汉时期我国酿酒工艺已经很成熟,谷物酒、配制酒、果酒、乳酒等种类众多,酿酒成为一个重要手工业,不仅有家用自酿、小酒肆、大酒家等私营酒业,还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严格的酒业管理体系,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官营酒业。从普通平民到宫廷皇室贵族,日常与节日宴饮均有规格、仪式不同的俗制,饮酒之风兴盛。汉高祖刘邦就很好酒,定鼎天下后过沛县,不忘与家乡父老子弟豪饮。“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酒俗的浓郁,酒业的发达,因之而生的佐酒之戏亦十分丰富,如酒令、六博、乐舞、投壶等。海昏侯墓也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青铜投壶,可见,游戏娱乐成为宴饮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西汉上层贵族阶级的闲逸生活方式、雍雅的酒俗文化。
二、储酒:形制多样的酒具
海昏侯墓不仅在北回廊酒具库中出土了酿酒的青铜蒸馏器,在东回廊厨具库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精美的储酒器具,如龙盘凤碗、耳杯、樽、卮等漆器,玉耳杯等玉器,还有青铜钫、青铜缶、青铜壶、青铜提梁卣等。
漆器方面,海昏侯墓除了出土有孔子画像漆木屏风、“四神”图像漆木屏风等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漆器外,还出土了一套精美的漆器厨具,尤其是龙盘凤碗一套,保存较好。龙盘“外黑内红”,颜色艳丽,底部有“三龙汇聚”图案,龙的形态清晰生动、栩栩如生;风碗造型别致,工艺纯熟,采用了夹丝胎工艺,口沿、底座、器身上都有银边装饰,碗底还刻有“绪银梳十枝”的字样。夹丝胎,简单来说就是用麻布和漆灰在内模上涂黏成型,待干燥后取出内模并再次探漆所形成的复合胎体。“漆器胎骨,完全用麻布和漆灰做成,称为‘夹丝’,又称‘脱胎’。”夹丝胎制作是漆器的一种重要工艺,既增加胎体的坚固性,又使胎体表面光滑美观。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较早的夹丝胎漆器大多在战国中后期,如1959年在湖南常德德山战国晚期墓发现深褐色朱绘龙纹漆,1964年长沙左家塘3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黑漆杯及彩绘羽觞等,都属于夹丝胎漆器。在汉代,漆器工艺比较成熟,在贵族阶层使用比较广泛,多用于妆、文房用品、酒具、屏风等生活器具。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龙盘风碗,采用龙凤图案及文字,使用夹丝胎工艺,堪称艺术珍品,显然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玉器方面,海昏侯墓也出土了一些旷世珍品,如憨态可掬的玉神兽、造型别致的龙风蝶形佩、镂刻精美的玉璇等,当然,在酒具中也出土了一件独特的玉器——玉耳杯。耳杯按材质可分为玉耳杯、漆耳杯、陶耳杯、铜耳杯。一般来说,材质的差异凸显使用者身份地位的高低。玉耳杯,始见于战国时的高级贵族墓葬,《中国文物大辞典》描述该器具,“饮酒器,其形俯视呈椭圆形,腹下略收,底有椭同形的圆足,或作平底,口两侧各有一形式相同的、半椭圆形耳。因两耳呈羽翅形,故名羽觞或耳杯”。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只玉耳杯玲珑剔透,弧形耳和杯底均有精美纹饰,反映了墓主的富足奢靡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信立祥认为这种玉耳杯是用于饮酒的,目前在汉代高级贵族墓葬中较少见,到东汉以后,类似随葬品多为冥器而非实用器,材质也多为陶质。
青铜器方面,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更是令人震惊,除出土了错金工艺精湛的博山炉,设计精巧的青铜雁鱼灯外,酒具也是类型多样、造型精美。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凤鸟纹提梁,这件精品文物的出土令学界十分惊诧,典型的商末周初时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了海昏侯的墓葬中?它和陕西梁带村出土的大凤鸟纹提梁直在形制上类似,提梁呈半圆弧型,提梁两端有兽首,直器身上的扉棱非常突出,直体上有精美的长尾凤鸟。一般来说,商代卣的凤鸟为短尾,西周时期则演变为长尾凤冠。据《中国文物大辞典》“铜卣”条注解:“容酒器。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和两周时期,到西周中期开始退出青铜器序列,春秋中期以后,又有少量出现在南方土墩墓中……延续时间较长、器型较多,有扁圆体卣、圆体卣、椭圆体卣、筒形卣、方体卣和鸟兽形卣诸类……商代晚期较常见的有扁圆体提梁卣和方腹体卣,还出现鸟兽形卣……提梁两端有兽首……卣的整体趋势足较为低矮,有敦实感,盖的形状较为丰满,多呈浑圆的帽状,盖两侧的角多有退化,器身多有铭义。”因此,海昏侯墓中出现商周时凤鸟提梁卣这种稀世珍品,也就不由得学界不惊诧了。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刘贺”玉印的发现及木牍奏章上“海昏侯臣贺”字样的频繁出现,人们的疑问也迎刃而解。刘贺,在位27天,生前经历了由昌邑王到汉废帝、再到海昏侯的跌宕起伏的沉浮人生。刘贺被废,“行昏乱”不过是一个借口,触及权臣霍光的利益才是被废的根本原因。从出土文物来看,作为上层贵族,刘贺必然循蹈于当时的贵族生活习俗,可能爱好收藏(出土的众多稀世珍宝),爱好音乐(出土的铁编钟、铁编馨、琴、瑟、笙、排箫)等,这样一些珍贵文物的出土,可能展示了刘贺生活的另一面。
青铜提梁卣这种珍贵的器具用来盛酒显得过于奢华,即便用来盛酒可能也只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笔者认为它更大可能是墓主生前喜欢的收藏品。除了青铜提梁卣外,在酒具库还出土了青铜钫、青铜缶、青铜壶等酒器,这些酒器纹饰厚重、庄严拙美,都是商周至汉代时期的重要酒器,是贵族阶层常用的酒具。
海昏侯墓出土的类型多样的雅致酒具,从漆器、玉器到青铜器,制作十分考究和完备,一方面反映了西汉社会酒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酿酒技术的进步、酒品类型的多样,还反映在酒具的形制追求,也是酒俗文化、宴饮仪式需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也烙下了时代的审美印记,酒具不仅是装酒的容器,也是一种生活审美,是主人身份、地位、爱好、情趣的展现,形式多样、技艺精湛、美观贵重的酒具,从侧面折射出西汉上层贵族的宴饮生活图景,海昏侯刘贺的独特身份,也投射出西汉社会酒俗文化的厚重内涵。
三、佐酒:风雅卫生的酒仪
饮酒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规范秩序的仪礼。《左传》载:“君子曰:酒成以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酒是用来完成仪礼的,不能过度饮用。在古代,“酒以成礼”,为佐礼之物,是一种沟通鬼神的媒介。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媒介功能逐渐减退,增进人际沟通及娱乐的功用越来越明显,但在某些正规场合,其佐礼的功能仍然有所体现,并没有完全丧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
在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有两套染炉,这种器物在江西汉代墓葬考古中是首次出土。染炉,由承盘(承接木炭灰)、染炉和染杯(耳杯)三部分构成,是炊器与食器的一种结合器具,为什么被称为染炉呢?此前有专家认为染炉为染色工具,后来有研究者否认了这种说法。笔者亦认为此种看法难以成立,理由有二:一是从染杯大小来看,大概可以盛装300毫升,且敞口较开,不宜进行染色操作;二是染炉在东回廊厨具库中出土,肯定与厨具有关联。染炉的由来还是得从其名称出发进行分析。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林已奈夫对“染”字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引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割鲜染轮”和《吕氏春秋·当务》中“具染而已”两处文献,指出“染”具有擩染、豉酱的意思。《礼记·内则》:“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里面的“醢”即酱的意思,就是将肉沾酱汁,这就是“染食”,这种享受美味的感觉亦如焦延寿所形象描绘的“一指食肉,口无所得。染其鼎鼐,舌馋于腹”的情状。因此,染炉的功用就是温热的作用,就餐时,染杯中预先盛放酱、盐的汁液,再将切成薄片的肉食放入,待其加热到一定程度,即可就食。由于染杯的容量很小,只适合个人食用,类似现在的单人小火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贵族阶层一种比较奢华的饮食器具。当然,染杯呈耳杯状,还有盛酒的功用,但并非是温酒器具,因为它是铜质的,加热太烫,不适合温酒,只适合一般饮酒所用。
染炉比较小,只能作为个人“染食”所用,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汉代饮食中的分食制。分食制,是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的一种饮食制度,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了孟尝君有贤名,在薛时门客众多,且待客甚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到”。如果是合桌共食的话就不会出现“饭不等”的情形,也就不会导致此类悲剧。对于汉代的分食制,我们很容易想起《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座位布置,在宴会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宴会上五人座位不仅是地位尊卑的显现,更是当时分食制的有力证明,一人一案。今天,在众多汉墓壁画、汉画像石、汉画像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席地而坐、一人一案、分案而食的宴乐场面。这也要求人们坐在席子上,席前置比较矮的几案,这种食俗规制在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也得以证实。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在主梓室出土了铜鼎、铜壶、染炉、耳杯等,还有几案。同时人们席地而坐,坐必有席,无席则无礼。席子不仅有材质的要求,如草席、竹席、苇席、兰席、桂席、苏熏席、象牙席等,而且对席镇也有讲究。席镇即镇压席子四角防止席子滑动或卷起的小饰件。如《酒赋》:“销绮为席,犀璩为镇。”《西京杂记》:“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席镇一般由陶瓷、玉石或金属等制成,多半做成鼓形、半圆形或动物形,以雕饰精美动物居多。海昏侯墓出了一批以鹿、龟、雁等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席镇。动物造型逼真、精巧雅致,如鹿的造型,富有动态感,鹿首向前昂扬,前腿微微蜷曲,后腿隐于身下,鹿后背有一凹槽,可能用于嵌入装饰物;如龟的造型,沉稳厚实、憨态可掬,龟背上镶嵌了一些宝石,如闪耀的鳞甲;如雁的造型,曲颈而卧,眼睛微睁,收翅凝神,生动安详。为何席镇要以鹿、龟、雁等动物为造型呢,可能和这些动物的象征寓意有关。鹿,在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在古墓发掘中也常发现以鹿为造型的器具及画像,这种现象说明古代鹿和人们的生活关系紧密,是重要的狩猎对象或肉食资源。鹿也是古代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的图腾,可从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的记载中推测。远古时期在内蒙古、新疆甚至南方等地区有以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或国家。还有鹿与“禄”谐音,与“官禄”联系,反映了古代社会追求仕途腾达的愿望及趋利求吉的民俗心理。龟,也和鹿一样,是图腾的产物,在古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鹿。龟是长寿、祥瑞和神灵的象征。《淮南子》曰:“龟三千岁。”《述异记》更是夸张地说,神龟寿五千岁,灵龟寿万年。龟也是祥瑞的表现,在古代和龙、麟、凤并称,号称“四灵”。龟还是神灵的象征,具有神秘的权威性,在商代,它具有特殊地位,国君对于不可决断的大事,都需要贞人集团用龟壳——龟卜来卜问天意吉凶。雁,与鹿、龟类似,又有所不同,寓意更鲜明,早在先秦时代,它就被赋予人格化形象并具有原始归属意向。儒家思想产生以后,儒士们迫切为其理论寻找合理依据,直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采纳天人感应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造和阐释,为儒学的正统化提供了理论基础。雁,定期南北迁徙的自然习性,是与儒家“信”的契合点。“雁在迁徙时,经常成群飞行,并在飞行中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雁的这种‘有序’的飞行方式,与儒家‘礼’的规范不谋而合。雁一般是一雄配一雌的,雌雄可能终生配对,双亲都参与幼鸟的养育。雁的这种失偶而不再配的习性,亦是儒家‘节’的要求。此外,雁的‘顺风而飞’、‘衔芦’及‘雁奴’的设置又体现了儒家‘智’的精神。”这样,雁的自然属性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象征寓意,具有儒家思想的意涵。因此,海昏侯墓席镇的鹿、龟、雁等造型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反映了西汉上层贵族向往长寿、吉祥及仕途腾达的心理。
染炉、席镇反映了分食制的特色,一人一席、席地而坐,但美味也不能一人独享,尤其是好友之间。有意思的是在海昏侯墓还出土了火锅状的青铜器温鼎,里面有板栗等残留物,考古专家初步认定它是当时的“火锅”。关于火锅的由来,只能依据文献记载进行推测,“鼎”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商周时期,“鼎”是重要的祭祀之器,兼具实用功能。据文献记载,古代在祭祀或庆典时,要“击钟列鼎”而食,可能和今天一样,众人围在鼎的周边,将肉食投入鼎中煮熟分食。火锅汤也被称为“骨董羹”,苏轼在《书陆道士诗》中记载:“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鲊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撅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在西南地区,火锅也被称为爨,南北朝时期该地少数民族被蔑称为獠,风俗规制荒蛮,“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日‘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三国时期,魏文帝为太子时曾经赠送钟繇一“五熟釜”,并书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维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这种炊具,一釜中有几格,可同时烹饪多物,类似于今天的分格火锅。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铜“火锅”,对于考证中国火锅史提供了一定的实物参考依据。当然,这种笨重的大“火锅”和分食制并不违背,它不适合个人食用,但可以通过用铜勺或匙将羹汤盛出,再分到各人的餐具中。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古代,乐和礼紧密相连,音乐是一种重要的仪礼,在海昏侯墓中还首次发现铁编磬,共出土三堵悬乐,两堵铁编钟,共24件,包括钮钟14件,大的甬钟10件,一堵铁编磬十多件,整套乐器保存完好,可以完整地奏出音乐。此外,还出土了完整的琴、瑟、排箫等乐器。可见,在西汉宫廷宴饮场合,即便是娱乐也要“不逾矩”,遵守宴饮俗制。上层贵族欣赏的钟磬之乐,并非单纯的通俗音乐,而是雅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虽然可以涮“火锅”,但亦不能大快朵颐,要遵守分食制,举手投足、行卧坐立均需谨遵宫廷酒俗规制。
小 结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它对于研究海昏文化,甚至整个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具有补遗的作用,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海昏侯墓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除了新媒体的积极跟踪报道外,还在于它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透过青铜蒸馏器、青铜提梁卣、青铜钫、青铜缶、玉耳杯、席镇、青铜“火锅”、铁编磬等珍贵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酒”文化的渗透力、生命力和规制力,从酿酒的青铜蒸馏器,到盛酒的青铜提梁卣、青铜钫、青铜缶、玉耳杯,再到佐酒的席镇、染炉、铜“火锅”、铁编磬等,一幅清晰的以“酒”为媒的贵族社会生活图景展现在世人面前,突出地展示了西汉酒俗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我们了解西汉社会打开了一扇“天窗”,也向我们展示着西汉上层社会的宴饮生活、宴乐图景。这些出土宴席酒具,从漆器、玉器到青铜器,并没有在时光中老去,无不鲜活地叙述着西汉时期斑斓的饮酒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西汉上层贵族奢华风雅的酒俗仪制与文化。这对我国饮食文化史研究,尤其是酒俗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和勾勒西汉贵族社会的民俗生活图景。
——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文明探源”栏目
特别提示:本文版权归作者/期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