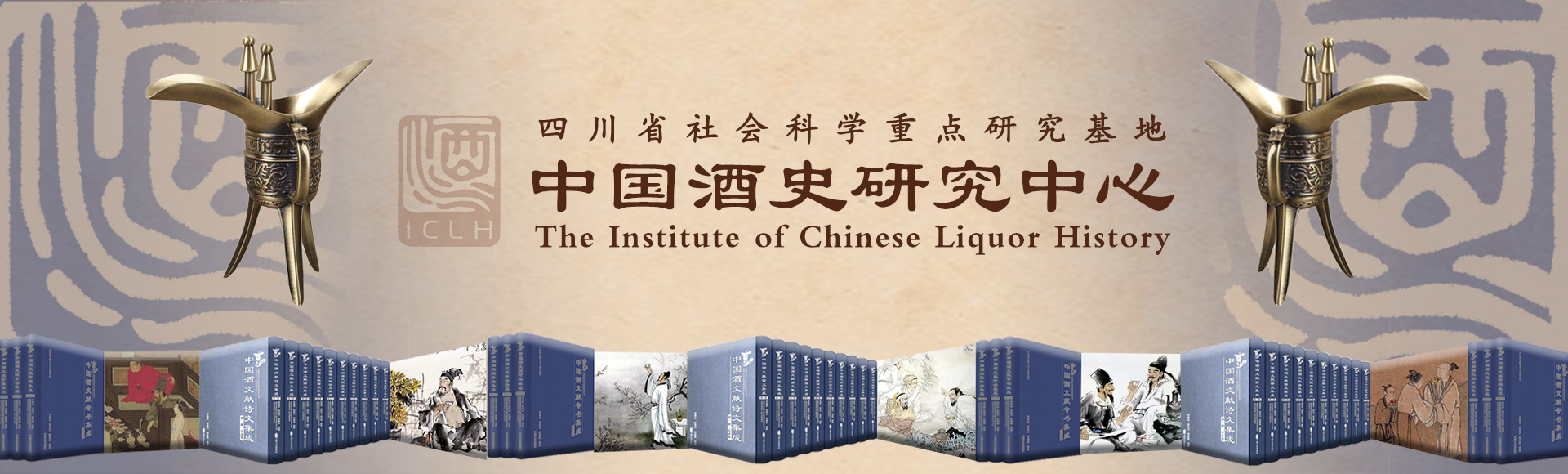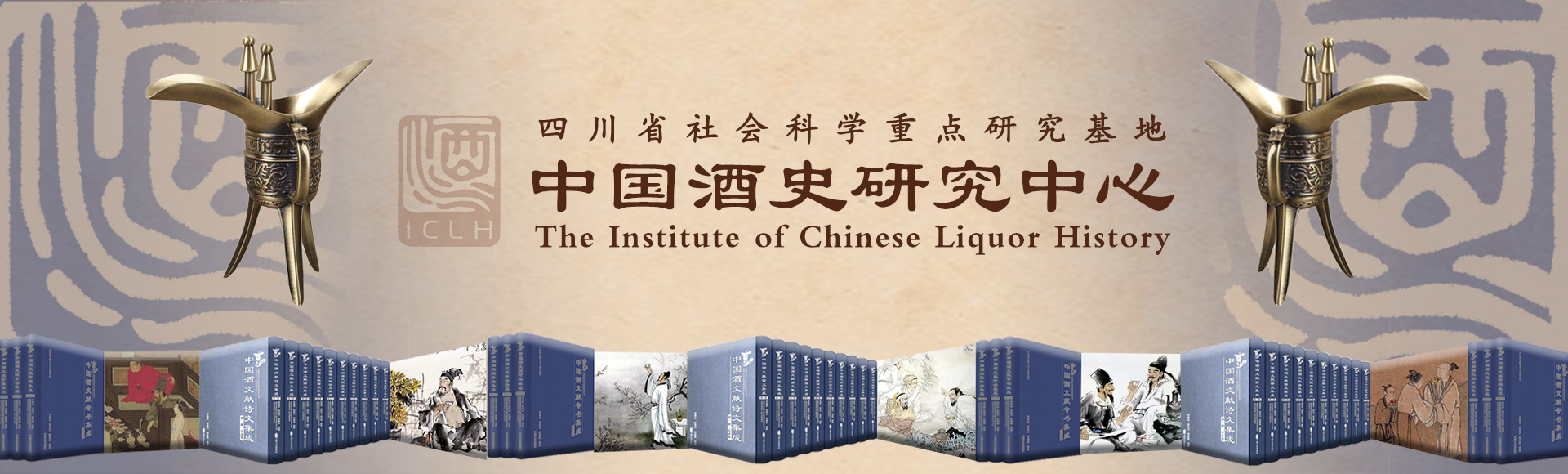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陆放翁《鹊桥仙》
到了绍兴,便喝上鉴湖水了。鉴湖,乃是萧山绍兴间的极大蓄水池,本来周围有百多里大,开辟于东汉年间。过去二千年间,四围土田逐渐被侵蚀,没有疏浚,面积缩小到后来,只剩下十五里长的清水湖了。这便是绍兴老酒的摇篮。
说到鉴湖的源流,张宗子就指出从马臻开鉴湖,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到了北宋,西湖夺取了她的宝座(西湖开辟于唐代);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了(这是张宗子的评语)。至于湘湖(在绍属萧山),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因此,韵士高人,谁也不曾着眼过。
在唐代,鉴湖和一位隐士贺知章有过一段因缘。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会稽人。官秘书监,天宝初请为道士,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刻川一曲。放翁那首词中的话,就是从这一故事翻出来的。(贺知章有一首《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乃是一直传诵的诗篇。)在我们记忆中,陆放翁与鉴湖的因缘,更是密切。我们出了绍兴偏门再向南走,便到了鉴湖,顺着湖边走三里路,便到了南宋诗人陆放翁故居——快阁。那是放翁晚年饮酒赋诗之地。本来有些假山、石桥和春花秋水楼、飞跃处等胜地,还有藏书满架的书巢。我们曾经在快阁逗留过了一晚,可是在抗战后期,日军进占绍兴时,“快阁”也就被破坏,化为陈迹了。放翁在《书巢记》中说:“……吾室之内,或栖于楼,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规,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搞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这倒是我所最欣羡的去处。
南宋淳熙八年(1181),放翁从江西回山阴,正月到家,这就是他经营快阁的开始,他曾写《小园》诗云: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
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历尽危机歇尽狂,残年唯有付耕桑,
麦秋天气朝朝变,蚕月人家处处忙。
村南村北鹑鸪声,水刺新秧漫漫平,
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放翁的另一遗迹,便是绍兴禹迹寺。故址上的沈园,那是他和被迫离去的妻子唐豌重逢之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有名的《钗头凤》悲剧,就在那儿上演的。“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混绞透”,我们的耳边,一直响着这一段哀歌(鉴湖,乃是放翁洒泪的伤心地)。
一植兰溪自献酬,祖年不肯为人留;
巴山频入初寒梦,江月偏供独夜愁。
——陆放翁《龟堂独酌》
我们翻看陆放翁的《剑南诗稿》,他有很多饮酒、醉中独酌的诗篇,这位诗人是会喝酒的。他颇欣赏金华兰溪的老酒,如这首诗所说的。在酒的历史上说,金华府属的义乌、兰溪,好酒的盛名,还早过了绍兴,唯一的反证就是那位葬在绍兴的大禹王,他是恶旨酒的,或许四千年前,绍兴已经酿酒了。放翁平常喝的,当然是绍兴本地的酒,他在《游山西村》中说:“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绍兴农村原是家家酿酒的。
绍兴酒是用糯米做的黄酒,和用麦或高粱做的烧酒,一辛辣,一醇甜,自是有别。绍酒之中,一般的叫花雕,坛上加花,原是贡品。(十斤装的叫京庄,专销京津;二十斤装的叫行使,专销湖广。目前小坛装的三斤,大坛装的二十五斤,上海南货店都有出售。)加料制造的,有善酿、加饭、镜面各品,酒味更醇。还有一种女贞酒,富家育女,便替她做酒加封,藏在地下,作为出嫁日宴客之用,故名女贞。酒越陈越香越醇,十年五年埋着,如《儒林外史》所写的杜家老太爷埋藏二十年的陈酒,镶了新酒,那几位酒翁,喝了才过瘾。
绍兴府属各县,都有绍酒酿坊,西郭、柯桥,沿鉴湖各村镇,散布很广;以东浦为最上,阮社次之,据说东浦以桥为界,内地也有上下床之分,那只好让行家去鉴别了。阮社村到处都是酿坊,满堤都是大肚子的酒坛,一眼看去,显得这是醉乡了。绍酒所以特别好,行家说主要条件之一是鉴湖水好。我的朋友施叔范,他是诗翁,也是酒伯。他说:真正的佳品,必须汲湖水酿造;水的成分不要过清,也不可过浊;清则质薄,日久变酸,浊则失掉清灵之气。鉴湖水,源出会稽,有如崂山泉,所含矿质,恰合酿酒之用,因此绍酒独占其美。(我个人的看法,金华酒并不在绍兴之下,只是产量不多,行销不广,让绍酒占尽声名而已。)
做酒是一种艺术。酿酒行家,叫缸头师傅。这种师傅我们家乡也有。首先把糯米浸了,再放上饭蒸(一种大木桶的蒸具)去蒸,蒸熟了,摊在竹垫上,等它凉下来,再拌上酒药;酒药的分量得有斟酌,多则味甜,少则味烈。接着把它放在大缸中“作”起来(“作”即是发酵之意)。究竟“作”多少日子,那就看缸头师傅的直觉判断了;总是听得缸中沙沙作响,有大闸蟹吐沫似的,看是“作”透了,再由酒袋装入酒架,慢慢榨出来。这榨入缸中的酒汁,一坛一坛装起来。再用泥浆封了口,一坛坛放入地窖中去,普通总是半年十月,就可开坛了;一年以上,便是陈酒,市上出售的,大多是一年陈的。我不会喝酒,却懂得做酒,因此,看看别人的描述,觉得不够切实。
“作”酒时期,我们也可喝连糟酒,称之为“缸面浑”,其味较醇,却不像“酒酿”那么甜。酿了头酒以后,还可再酿一次,其味淡薄,我们乡间,称之为“旁旁酒”(不知究竟该怎么写)。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那八位酒鬼都很有趣。不过,他们喝的不是绍兴酒,汝阳王李碰,他要去的是想“移封向酒泉”(今甘肃),并非到绍兴。我不会喝酒,要喝还是喝绍兴老酒。绍兴老酒,我说过是一种糯米酒,味儿醇厚,黄澄澄地。我喝过一坛十五年陈的枣酒,那简直像酱油一般。我们一想到茅台、大曲、汾酒、高粱那股辛烈的冲劲,就觉得冬日跟夏日的不同。我们喝绍兴酒,总是一口一口地喝,让舌尖舌叶细细享受那甜甜的轻微刺激,等到喝得醉醺醺时,一种陶然的心境,确乎飘飘欲仙。我们从不像欧美人那样打开了瓶嘴,尽自向肚子灌下去,定是要喝得狂醉了才罢手的。鲁迅曾在一篇小说中,写他自己走上了一石居小酒楼,坐在小板桌旁,吩咐堂馆:“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他很舒服地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这就是酒客的情调了。在绍兴喝酒的,多用浅浅的碗,大大的碗口,一种粗黄的料子,跟暗黄的酒,石青的酒壶,显得那么调和。
要说绍兴酒店的格局,鲁迅在《孔乙己》那小说的开头,有过如次的描写: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店的后半雅座,摆上几个狭板桌条凳,可以坐上八九十来个人,就算是很宽大的了。下酒的东西,顶普通的是鸡豆与茴香豆。鸡豆乃是白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以细草纸包作粽子样,一文一包,内有豆可二三十粒。茴香豆是用蚕豆即乡下所谓罗汉豆所做,只是干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只是一文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抓;伙计也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盐豆玻等,大体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我们家乡的酒店,也是这么一个格局,假使《孔乙己》要上演,这样布局是不可少的。
说到孔乙己喝酒的咸亨酒店,周启明先生还写了几段小考证:咸享酒店开设在东昌坊口,坐南朝北,店堂的结构与北京的大酒缸不相同。在上海一带那种格式大抵是常有的。——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台边有一两人站着喝碗酒。那情形也便差不多了。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样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做窜筒,读如生窜面的窜,却是平声。圆筒内盛酒拿去放在盛着热水的桶内,上边盖板镂有圆洞,让圆筒下去,上边大的部分便搁在板上。这么温了一阵子,酒便热了。一窜筒的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制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酒盏吧。
绍兴人喝黄酒,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喝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
——选自《万里行记》,三联书店2000年版